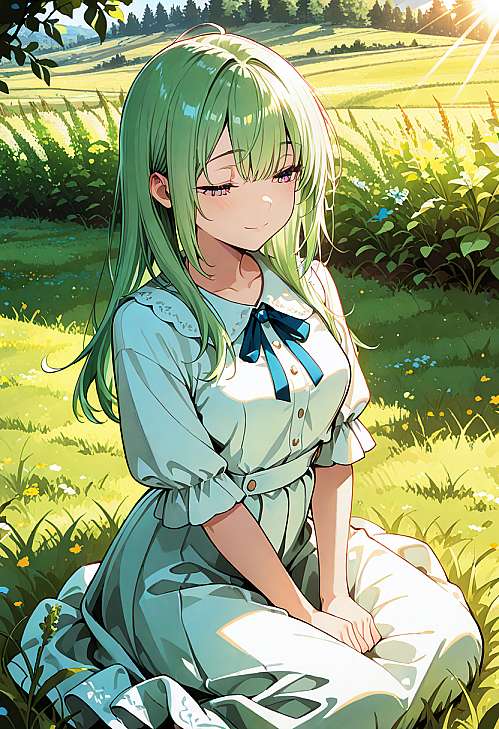前世被丈夫和妹妹联手做成人彘,只为逼问祖传苏绣秘技。重生回订婚宴,我当众掀了桌子。
“不如先解释解释,你书房暗格里那本《如何让女人心甘情愿交出传家宝》?
”后来京城最神秘的绣坊突然放出绝世双面三异绣。曾经欺我辱我之人,
正跪在雪地里求我刺一针。而新帝最宠信的年轻宦官,却低头为我穿针引线:“娘娘,
这批‘人皮绣布’…您还满意吗?”剧痛是从四肢的断裂处开始的,像烧红的铁钎,
反复捅穿碾磨。然后才是无边无际的黑暗,黏稠、窒息,灌满口鼻。
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血腥,还有金疮药也无法掩盖的、皮肉腐烂的甜腥气。
沈青瓷知道自己还活着,以一种比死更不堪的姿态。她躺在一个特制的陶瓮里,
瓮口齐着她的肩膀。眼睛……早已没了,只剩两个空洞的窟窿,
偶尔能感到湿冷的空气流进去。耳朵却异常灵敏,能听见不远处炭火盆里哔哔的轻响,
能听见自己残破躯干里,心脏微弱而固执的跳动,还有那两个人的声音。
“……还是不肯说么?”是林维舟,她的丈夫,声音一如既往的温醇,
此刻却透着不耐烦的冷,“青瓷,你这又是何苦?沈家‘织云变幻手’的秘技,你一个女子,
留着又有何用?交给我,林家绣坊便能更上一层楼,于你,也算是功德一件。”功德?
沈青瓷想笑,喉咙里却只能发出嗬嗬的漏气声。功德就是趁她染病体弱,
与她的好妹妹沈白芷联手,用药迷倒她,斩去她的四肢,做成人彘,囚在这不见天日的密室,
日**问?“姐姐,你莫要再固执了。”沈白芷的声音响起,娇柔婉转,
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与心疼,仿佛她才是那个受尽折磨的人,“姐夫也是为你好,为沈家好。
你看你现在……说出来,姐夫定会好好待你,给你用最好的药,
让你……舒舒服服地走完最后一程。”沈青瓷残存的躯体轻轻颤抖起来,不是因为恐惧,
而是恨,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冲破这具破烂的皮囊。她想起来了,那本被沈白芷“偶然”发现,
又“羞红着脸”偷偷塞给林维舟的春宫绣样图册,原来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
林维舟书房暗格里,哪是什么风月闲书,那本她曾无意瞥见书名便不敢再看的册子,
真正名字该是《如何驯服与攫取——女子家传秘技攻心术》吧?更早的时候,
母亲身体莫名衰败,父亲珍藏的绣谱离奇失踪……一桩桩,一件件,原来早就织成了一张网,
只等她这只蠢雀一头撞进来。她好恨。恨林维舟的虚伪狠毒,恨沈白芷的贪婪阴险,
更恨自己的眼盲心瞎!为何看不清身边豺狼的嘴脸?为何将母亲临终前紧握她手,
那句“青瓷,沈家真正的‘织云变幻手’,不在绣谱,在你的心,你的手,你的血性里。
非到万不得已,宁绝勿传!”的叮嘱,忘在了脑后?“青瓷,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”林维舟的脚步声靠近,停在陶瓮边,阴影笼罩下来,
“说出‘织云变幻手’的引线诀与分光秘法,我给你一个痛快。
”嗬……嗬……沈青瓷用尽残存的力气,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,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。
“冥顽不灵!”林维舟声音陡然转厉,“白芷,拿盐水来!再不说,
就让她尝尝这伤口日日新鲜溃烂的滋味!”“是,姐夫。”沈白芷的应声里,
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。盐水浇灌的刺痛尚未落下,
一阵更尖锐、更彻底的剧痛猛地从心口炸开!像有什么东西,生生剜走了她仅存的支撑。
黑暗彻底吞没意识前,她仿佛听见沈白芷惊慌的声音:“姐夫!她的心口……那是什么?
”是什么?是她沈家女儿,生来心口便有的那一点朱砂胎记,形如未绽的青瓷盏中,
一滴凝血。也好。这肮脏的躯壳,这被谎言与背叛蛀空的人生,不要也罢。
若有来世……若有来世!林维舟,沈白芷,我要你们血债血偿!我要你们所求皆空,
所拥尽碎!我要你们……堕入无间,永世不得超生!·“小姐?小姐?您怎么了?
可是身子不适?”略显急促的呼唤,伴随着衣袖被轻轻拉扯的触感,
将沈青瓷从无边的黑暗与剧痛中猛地拽回。视线先是一片模糊的光晕,继而渐渐清晰。
刺目的红,铺天盖地的红——眼前是厚重的、绣着并蒂莲的大红桌帷,
身下是坚硬的、同样铺着红缎的楠木椅子。空气中飘浮着酒菜的香气、脂粉味,
还有嘈杂的、刻意压低的谈笑声。她僵硬地、极其缓慢地转动脖颈。映入眼帘的,
是一张写满担忧的熟悉脸庞——丫鬟碧珠,十四五岁年纪,眼睛圆圆的,
此刻正焦急地望着她。碧珠……她不是在三年前,因为“偷窃”沈白芷的一支簪子,
被活活打死了吗?沈青瓷猛地低头,看向自己的手。那是一双少女的手,肌肤细腻,
指节匀称,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,透着健康的淡粉色。没有血迹,没有伤痕,
更没有那日复一日被银针挑破指尖、逼问分光针法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旧疤。
她的手……她急急又去摸自己的腿,隔着层层叠叠的嫁衣布料,能清晰地感受到腿的存在,
完整,有力,甚至能随着她的意念轻轻移动脚尖。不是空荡荡的,
不是那只剩下丑陋断茬、泡在脓血里的残肢!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,撞得耳膜嗡嗡作响,
几乎要喘不过气。她抬手,按向自己的心口。隔着重重的衣料,
指尖似乎能感受到那一点熟悉的、微凸的轮廓。朱砂胎记还在。她抬眼,目光掠过碧珠,
看向四周。这里是……林府正厅?不对,是林府宴客的花厅。厅内张灯结彩,红烛高烧,
宾客满座。主位上,她的父亲沈文柏正与林维舟的父亲林老爷把酒言欢,
脸上是掩不住的、对未来亲家与这门婚事的满意。母亲的位置空着……是了,
母亲早在她及笄前一年便病故了。而坐在她左手边下首位置的,
是一身娇俏水红衣裙、正侧头与邻座一位夫人低声说笑、眉眼弯弯的沈白芷。她的好妹妹。
再看自己身上——大红的嫁衣,繁复的苏绣花纹,用的是顶好的软烟罗和流光锦,针脚细密,
图案吉祥。这是她及笄后,花了整整一年时间,一针一线为自己绣的嫁衣。前世的今天,
就是她与林维舟的订婚宴。记忆的碎片轰然拼合。是了,就是今天。吉时已到,宾主尽欢,
酒过三巡,即将交换信物、正式落定婚约的前一刻。她回来了。
重生在了这个决定她前世悲惨命运的节点!一股冰寒彻骨的冷意,顺着脊椎猛地窜上头顶,
随即又被胸腔里轰然燃起的、近乎焚烧一切的炽烈恨意所取代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
刺痛带来一丝畸形的清醒。她不能慌,不能乱。上苍给了她重来一次的机会,
不是让她再来哭诉一遍委屈,再走一遍绝路!她要报仇。就从此刻,此地,
撕开这虚假的喜庆,撕碎那对狗男女伪善的面皮开始!“姐姐,你脸色好白,是不是累了?
”沈白芷不知何时转过头来,声音柔婉,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切,伸手似乎想探她的额头,
“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,可要撑住呀。”沈青瓷微微偏头,避开了她的手。动作不大,
却带着明显的疏冷。沈白芷的手僵在半空,脸上闪过一丝错愕,随即化为更深的担忧,
眼眶甚至微微红了:“姐姐……”这一番动静,引得附近几桌的宾客也侧目看来。
主位上的林老爷哈哈一笑,打圆场道:“青瓷丫头怕是害羞了。维舟,
还不快去关心关心你未来的新娘子?”坐在父亲下首的林维舟应声起身。
他今日一身靛蓝暗纹锦袍,衬得身姿挺拔,面如冠玉,嘴角噙着温和的笑意,眼神深邃,
确是一副翩翩佳公子的模样。前世,她就是溺毙在这双看似深情的眼睛里。
他步履从容地走到沈青瓷面前,微微俯身,声音压低,确保只有近处几人能听清,
语调温柔得能滴出水来:“青瓷,可是身子不适?若实在撑不住,我扶你先去后堂歇息片刻?
吉时……耽搁一会儿也无妨的。”多么体贴,多么周全。前世,她就是被这番“体贴”蛊惑,
强忍着莫名的心悸与不安,点头应允,被他半扶半抱地带离了宴席,
也从此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沈青瓷抬起头,看向林维舟。她的目光很静,
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,底下却翻涌着足以吞噬一切的黑暗。脸上没有新嫁娘的娇羞,
也没有身体不适的虚弱,只有一种近乎漠然的审视。林维舟被她看得心头莫名一突,
那眼神……太过陌生,全然不似平日里沈青瓷看他时,那种仰慕中带着怯意的温柔。
“林公子。”沈青瓷开口,声音不大,却因厅内短暂的安静而显得清晰。
她没有用更亲密的称呼。林维舟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,随即笑得更温柔:“怎么了?
青瓷,你我是未婚夫妻,何必如此见外。”沈青瓷缓缓站起身。嫁衣长长的裙裾拂过地面。
她没有理会林维舟伸过来的手,而是转向主位,对着沈文柏和林老爷,福了福身。“父亲,
林世伯。”沈文柏见她举止有异,心中不悦,但碍于场合,只得端着笑容:“青瓷,
有话但说无妨。”沈青瓷直起身,目光扫过满堂宾客。
那些或好奇、或打量、或带着暧昧笑意的目光,此刻在她眼中,
皆成了这场盛大虚伪戏剧的看客。她深吸一口气,再缓缓吐出。开口时,声音清亮,
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,清晰地传遍花厅每一个角落:“这门亲事,我不同意。
”“哗——”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满厅的喧哗谈笑戛然而止,瞬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。
所有人都惊呆了,难以置信地看着站在厅中,一身大红嫁衣却面色冰寒的沈家大小姐。
沈文柏脸上的笑容僵住,随即涨得通红,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:“青瓷!你胡说什么!
婚姻大事,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岂容你儿戏!”林老爷的脸色也沉了下来,
目光锐利地看向沈文柏:“沈兄,这……是怎么回事?”林维舟更是愕然当场,
他万万没想到,一贯柔顺怯懦的沈青瓷,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,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来。
他脸上的温柔面具出现裂痕,上前一步,试图去抓沈青瓷的手腕,
声音带上了几分严厉:“青瓷!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快向父亲和林世伯道歉,
收回刚才的话!你定是病糊涂了!”沈青瓷再次避开他的手,甚至后退了半步,拉开距离。
她看向林维舟,嘴角勾起一抹极淡、极冷的弧度。“病糊涂了?”她重复着,
眼神如淬毒的针,“林公子,比起我是否病糊涂,不如你先向诸位解释解释——”她顿了顿,
目光扫过竖起耳朵的宾客,一字一句,清晰无比地问道:“你书房西墙博古架后,
那道暗格里,藏着一本名为《如何驯服与攫取——女子家传秘技攻心术》的书册,
里面详细记载了如何接近、骗取、操控身负家传技艺的女子,最终使其心甘情愿交出秘技,
甚至……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的法子。”“这本书,”沈青瓷的声音陡然拔高,
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,“你又该如何解释?与我沈家订婚,究竟是为了我沈青瓷这个人,
还是为了我沈家那‘织云变幻手’的刺绣秘技?!”死寂。
比刚才更彻底、更令人窒息的死寂。
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、骇人听闻的指控震得目瞪口呆。窃取家传秘技?这等行径,
在注重技艺传承、视秘技如性命的匠作行当里,是比偷盗财物更令人不齿的阴毒算计!
若真如此,林家声誉将扫地殆尽,林维舟此人,更是心术不正,禽兽不如!林维舟如遭雷击,
脸色“唰”地一下变得惨白,血色尽褪。他瞳孔骤缩,惊骇万分地瞪着沈青瓷,
像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她。那本书……那本书他藏得极其隐秘,
连贴身心腹小厮都不知具体位置,沈青瓷是如何得知的?!
难道她……她偷偷潜入过自己的书房?不可能!她哪有那个胆子,又哪有那个本事?
“你……你血口喷人!”巨大的恐慌和难以置信让林维舟的声音都变了调,尖利而扭曲,
“沈青瓷!我与你无冤无仇,你为何要如此污蔑于我!那是什么邪书?我听都没听过!
定是你不想嫁我,编造出此等荒谬绝伦的借口!”“污蔑?”沈青瓷冷笑,眼神锐利如刀,
刮过林维舟惊慌失措的脸,“那本书,蓝色封皮,无署名,以仿宋体手抄,共七十八章。
第三章专论‘示弱与体贴,卸其心防’,第五章详解‘制造危机,孤立其势’,最后一章,
甚至记载了数种前朝失传的、能令人神智昏聩、吐露真言的秘药配方……林公子,
需要我一章一章,背给在场的诸位叔伯长辈听听么?”她每说一句,林维舟的脸色就白一分,
身体几不可察地颤抖起来。那些内容……她竟然真的知道!她怎么可能知道得如此详细?!
厅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,看向林维舟的目光充满了惊疑、审视和鄙夷。
沈青瓷的描述太具体了,不似临时编造。若她所言非虚……沈文柏也惊呆了,
他看看面如死灰、哑口无言的林维舟,又看看神色冰冷、言之凿凿的女儿,
一时竟不知该信谁。但沈青瓷列举的细节,实在不像一个深闺少女能凭空捏造出来的。
“还有你,我的好妹妹。”沈青瓷不等林维舟辩驳或者说,他已震惊失语,无从辩驳,
目光如冰锥般刺向一旁早已吓得魂飞魄散、花容失色的沈白芷。沈白芷被她看得浑身一哆嗦,
下意识地往后缩,
的无辜委屈快要挂不住:“姐、姐姐……你怎能如此说姐夫……你定是误会了……”“误会?
”沈青瓷一步步走向沈白芷,嫁衣曳地,竟走出了一种逼人的气势,“去年春日,
母亲病榻前那碗本该由我侍奉的汤药,是你主动接过,说‘姐姐累了一夜,让我来吧’。
母亲喝下那碗药后,不过两个时辰便呕血昏迷,三日後溘然长逝。事后你哭得死去活来,
说是药房抓错了药,父亲怜你年幼失察,只罚了药房伙计。可那日你端药前,
指甲缝里沾着的‘灰线草’粉末,又作何解释?那东西单用无害,
与我母亲常年服用的‘雪参养荣丸’相遇,便是催命剧毒!”“你胡说!我没有!
”沈白芷尖声叫起来,脸色惨白如鬼,眼泪扑簌簌落下,是真正的恐惧之泪,“爹爹!爹爹!
姐姐她疯了!她污蔑完姐夫又来污蔑我!女儿没有!女儿怎么会害母亲!那是我们的亲娘啊!
”她扑向沈文柏,哭得撕心裂肺。沈文柏被这接连的指控震得头晕目眩,尤其涉及亡妻死因,
更是心神巨震。他看着哭成泪人的小女儿,
又看看神色决绝、眼神清明毫无疯癫之色的大女儿,一时心乱如麻。
沈青瓷却不再看他们父女,倏然转身,面向满堂宾客。她脊背挺得笔直,
像一杆宁折不弯的枪。“诸位叔伯,诸位亲朋。”她声音朗朗,压下满厅哗然,“今日之事,
匪夷所思,惊扰各位雅兴,青瓷在此赔罪。”她再次敛衽一礼,姿态无可挑剔,
却带着一种凛然不可犯的孤绝。“然,林家公子心怀叵测,觊觎我家传之秘,行径卑劣,
令人齿冷!沈白芷,谋害嫡母,其心可诛!此等人家,此等亲眷,我沈青瓷,耻与为伍!
”话音落下,她猛地抬手,抓住铺着大红桌帷的宴席边缘,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,
用尽全身力气,狠狠向上一掀!“轰隆——哗啦啦!”杯盘碗盏,珍馐佳肴,汤水酒液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