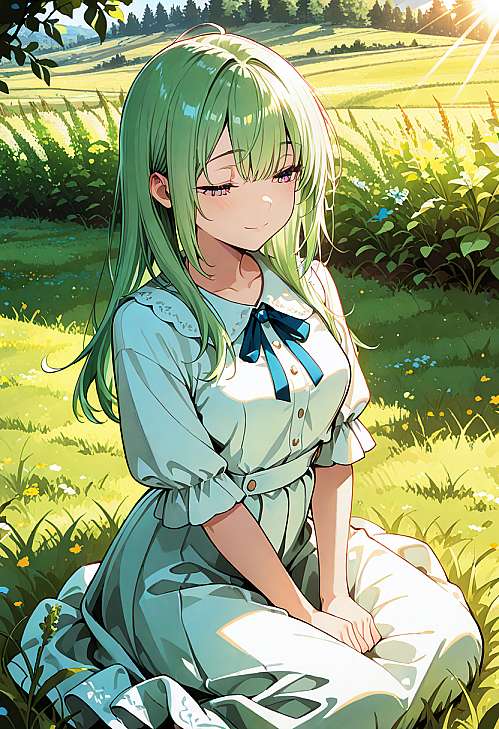冷宫重生冷宫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,沈芷寒睁开眼,手指还压在胸口,
那里残留着灼烧般的痛。她没死。她活过来了。屋内灰暗,墙角堆着发霉的被褥,
窗纸破了几个洞,风从缝隙钻进来,吹得烛火摇晃。她撑着身子坐起,手背蹭过粗糙的床板,
留下一道红痕。她没喊疼,也没哭,只是盯着自己的手——这双手还没沾血,
还没被人踩进泥里。她走到铜镜前,镜面模糊,映出一张苍白的脸。眉目未损,唇色尚存,
没有溃烂,没有浮肿。她伸手摸了摸脸颊,指尖冰凉。这不是梦。她真的回来了,
回到中毒前三天。门外传来脚步声,不轻不重,停在门口。沈芷寒没回头,
继续看着镜中自己。脚步声犹豫了一下,又退远了。
她知道是谁——是那个每日送馊饭的老太监,怕她疯,更怕她死。她转身走向桌边,
掀开食盒盖子,里面是半碗冷粥,几根咸菜。她端起来,一口一口吃干净。
咽下去的时候喉咙发涩,但她没停。饿不死,才能报仇。吃完,她把碗放回食盒,
用袖子擦了擦嘴角。然后走到墙角,蹲下身,从砖缝里抠出一块松动的青砖。
砖后藏着半截炭条,是她前世藏下的。她捏着炭条,在墙上划了一道竖线。这是第一天。
她站起身,拍掉手上的灰,低声说:“赵德妃,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”她没喊,没骂,
声音轻得像风,却带着铁锈味。她记得赵德妃是怎么笑的——在她毒发抽搐时,站在冷宫外,
隔着门缝说“沈家的女儿,就该这么死”。她也记得太子那张假仁假义的脸,
递给她那杯毒茶时,还说什么“表妹保重”。她走到窗边,推开半扇窗。风灌进来,
吹乱她的头发。她望着远处宫墙,那里灯火通明,丝竹声隐约可闻。那是赵德妃的寿宴,
满朝文武都在恭贺,没人记得冷宫里有个快死的废相之女。她关上窗,走回床边坐下,
从枕下摸出一块碎瓷片。锋利的边缘割破指腹,血珠冒出来,她没皱眉,只是盯着那抹红,
低声说:“这一世,我要你们跪着看我站起来。”门外又传来脚步声,这次不止一人。
沈芷寒把瓷片藏回枕下,躺回床上,闭上眼装睡。门被推开,两个宫女提着灯笼走进来,
一个手里端着药碗。“主子说了,今日的药不能断。”年长的那个说。“她都这样了,
还喝什么药?”年轻的嘀咕。“少废话,灌下去就是。”沈芷寒猛地睁眼,坐起身,
直勾勾盯着她们。两个宫女吓了一跳,药碗差点脱手。“我自己喝。”她说。
年长的宫女愣了一下,把药碗递过去。沈芷寒接过,一饮而尽。药很苦,她咽得干脆。
宫女们对视一眼,匆匆退了出去。门刚合上,沈芷寒就冲到墙角,抠着喉咙把药全吐了出来。
她喘着气,抹掉嘴角残液,冷笑了一声。这药里没毒,但加了让人昏睡的料。
赵德妃想让她在冷宫里无声无息地睡死过去。她走回床边,重新躺下,手伸进被褥,
摸到那块炭条。她在床板背面又划了一道。第二天。夜深了,宫里的喧闹渐渐平息。
沈芷寒睁着眼,听着屋顶老鼠爬过的窸窣声。她没睡,她在等。等一个人。三更梆子刚响,
窗棂轻轻一动。一道黑影翻窗而入,落地无声。那人蒙着面,只露出一双眼睛,冷得像刀。
“七殿下派我来问,姑娘可愿合作?”黑影声音压得很低。沈芷寒坐起身,
盯着他:“回去告诉萧景珩,我要活的赵德妃,死的太子党。他若答应,明日此时,
我给他第一份礼。”黑影没动,似乎在等她继续。“告诉他,我知道他母妃当年是怎么死的。
”她说。黑影眼神一变,转身跃窗而出,消失在夜色里。沈芷寒重新躺下,手按在胸口。
那里不再痛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滚烫的火。她闭上眼,嘴角微微扬起。这一世,
她不会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。她要让所有人知道,废相之女,也能掀了这东澜王朝的天。
装病藏锋黑影离开后,沈芷寒没再躺下。她坐在床沿,盯着门缝外透进来的微光,
耳朵捕捉着屋外每一丝动静。脚步声远了,灯笼的光也灭了,冷宫重新归于寂静。
她起身走到桌边,把药碗端起来,倒扣在掌心,轻轻晃动,让残液滴落在指尖。她舔了一下,
苦味里带着一丝腥气,和前世毒发前喝下的那碗一模一样。她把碗放回原处,
从枕下抽出碎瓷片,在床板背面又划了一道。这是第三天。
她知道赵德妃不会让她活过第五天——前世就是第五天夜里,她浑身抽搐,口吐黑血,
死在无人问津的破床上。这一世,她必须在那之前拿到证据。天刚亮,送药的宫女又来了。
还是昨天那个年长的,身后跟着个面生的小丫头,低着头,手有点抖。沈芷寒靠在床头,
脸色比昨日更差,嘴唇发白,呼吸轻得几乎听不见。“姑娘,该喝药了。
”年长宫女把药碗放在桌上,语气平淡,眼神却往床角扫了一圈。沈芷寒没应声,
等了一会儿才缓缓抬手,接过药碗。她喝得很慢,一小口一小口地咽,眼睛始终垂着,
像是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。喝到一半,她手一抖,药碗脱手砸在地上,汤汁溅了一地,
瓷片四散。“哎呀!”小丫头惊叫一声,慌忙蹲下去收拾。
年长宫女皱眉:“怎么这么不小心?”沈芷寒咳嗽两声,声音虚弱:“我……手滑了。
”小丫头手忙脚乱地捡碎片,沈芷寒趁机用脚尖把一片沾着药渣的瓷片往床底踢了踢,
然后伸手去扶床沿,假装要起身帮忙。她身子一歪,整个人摔在地上,额头磕在桌腿上,
发出闷响。“别动她!”年长宫女喝止正要上前搀扶的小丫头,“主子交代过,她若出事,
咱们都得陪葬。”小丫头吓得缩回手,站在原地不敢动。沈芷寒趴在地上,闭着眼,
呼吸急促,像是晕过去了。年长宫女蹲下来探了探她的鼻息,确认她还活着,才松了口气,
转头对小丫头说:“去禀报主子,就说人没事,只是摔晕了,药洒了,
今日的量已经喂进去大半。”小丫头点头,转身快步离开。等人走远,沈芷寒才慢慢睁开眼。
她撑着地面坐起来,背对着门口,手指悄悄伸进袖口,从内衬夹层里摸出一块布巾,
把刚才藏在指缝间的半片药材裹住,塞进腰带暗袋。那药材边缘泛黑,气味刺鼻,
和她前世临死前在药渣里发现的一模一样。她重新躺回床上,拉过被子盖好,闭上眼装睡。
没过多久,窗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,很轻,但刻意压低反而显得突兀。沈芷寒没动,
只把眼睛睁开一条缝,透过窗纸的破洞往外看。一个穿深蓝宫装的女人站在院墙拐角,
侧脸对着这边,目光直勾勾盯着窗户。那是赵德妃身边最得力的掌事姑姑,姓柳,
专管后宫阴私事。柳姑姑站了一会儿,见屋里没动静,才转身离开。沈芷寒等她走远,
才彻底睁开眼。监视的人来了,说明赵德妃已经开始紧张。她不怕被盯,
怕的是对方不动手——不动手,她就抓不到把柄。午后,送饭的老太监来了,
食盒里多了碗姜汤。沈芷寒没碰,只吃了半碗粥。老太监收碗时看了她一眼,欲言又止,
最后叹了口气,低声说:“姑娘,能熬一天是一天。”沈芷寒没答话,等他走了,
才从床底拖出那片沾着药渣的瓷片,用指甲刮下一点残渣,包进布巾,
和那半片药材放在一起。她需要有人帮她验这东西——苏挽晴是太医院的人,
但眼下她出不去,苏挽晴也进不来。她得想办法把东西送出去。傍晚,
她听见院外有扫地的声音。是个新来的粗使宫女,年纪不大,干活毛躁,
扫帚刮在地上哗啦作响。沈芷寒走到窗边,轻轻敲了敲窗框。扫地声停了,宫女抬头看过来。
“你,过来。”沈芷寒声音很轻,但足够清晰。宫女犹豫了一下,放下扫帚,
磨蹭着走到窗下。“帮我带个口信给太医院的苏医官,
就说……我梦见她送我的那支梅花簪断了。”沈芷寒说完,从袖中摸出一枚铜钱,递出窗缝。
宫女盯着铜钱,没接。“事成之后,另有重谢。”沈芷寒补充。宫女咬了咬嘴唇,
终于伸手接过铜钱,攥在手心,点点头,转身快步走了。沈芷寒退回屋里,坐回床边。
梅花簪是她和苏挽晴之间的暗号——簪断,代表性命危急,需立刻援手。苏挽晴收到消息,
一定会想办法进来。夜深了,沈芷寒没睡。她坐在桌边,把药材残片摊在掌心,反复查看。
这东西她认得,是“乌骨藤”,本身无毒,但和另一种药材“赤霜草”同服,会化成剧毒,
三日之内脏腑溃烂而亡。前世她就是死在这上面。赵德妃很聪明,分两次下药,
先让她喝含赤霜草的补汤,再在风寒药里加乌骨藤,外人看来只是病重不治,
查不出人为痕迹。她必须赶在第三剂药送来前,让苏挽晴拿到证据。三更天,窗棂又动了。
这次不是黑影,是苏挽晴。她穿着夜行衣,脸上蒙着布,
翻窗进来时差点被地上的碎瓷片绊倒。“你疯了?”苏挽晴压低声音,
“冷宫现在被盯得这么紧,你还敢传信?”沈芷寒没废话,直接把布巾递过去:“验这个。
”苏挽晴打开一看,眉头立刻皱起来:“乌骨藤?谁给你开的药?”“赵德妃的人。
”苏挽晴倒吸一口凉气:“她想让你悄无声息地死。”“我知道。”沈芷寒盯着她,
“你能把这东西带出去吗?”苏挽晴把药材重新包好,塞进自己袖袋:“明天我值夜,
有机会。但你得给我争取时间——如果赵德妃发现药材丢了,一定会提前动手。
”“我会拖住她。”沈芷寒说,“你只需要做一件事:把这东西交给周砚,
让他找可靠的人验明毒性,留作证据。”苏挽晴点头:“还有别的吗?”“告诉萧景珩,
我要的东西,今晚必须送到。”苏挽晴愣了一下:“你真信他?”“我不信他,
但我信他想扳倒赵德妃。”沈芷寒冷笑,“他母妃的死,和赵德妃脱不了干系。这笔账,
他比我更想算。”苏挽晴没再说什么,转身跃窗而出,消失在夜色里。沈芷寒重新躺回床上,
手按在胸口。那里跳得很快,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因为兴奋。棋局开始了,第一步棋,
她已经落下。赵德妃以为她在等死,殊不知,她正在织一张网,而第一根线,
已经缠上了对方的脖子。门外,又传来脚步声。这次不止一人,还有低语声。沈芷寒闭上眼,
呼吸放轻。门被推开,火光映在墙上,晃动的人影投在床前。“还活着。”一个男声说。
“主子说了,明日的药,加双倍乌骨藤。”另一个声音回答。“不怕她察觉?
”“一个将死之人,察觉了又能如何?”脚步声退去,门被轻轻带上。沈芷寒睁开眼,
嘴角微微扬起。他们果然着急了。越急,越容易出错。她等的就是这个。
她从被褥下摸出炭条,在床板背面划下第四道。明天,就是第五天。前世她死在这一天,
这一世,她要让赵德妃开始害怕这一天。窗外,月光被云遮住,冷宫陷入更深的黑暗。
沈芷寒却觉得,天快亮了。医官之盟门轴轻响,苏挽晴提着药箱跨进门槛时,
沈芷寒正靠在床头,手里捏着半块干饼,慢条斯理地嚼着。她没抬头,只把饼屑抖进掌心,
拢成一小堆。“装得挺像。”苏挽晴放下药箱,顺手把门掩上,
“连柳姑姑都骗过去了——你额头那道红印,是故意磕的吧?”沈芷寒咽下最后一口饼,
拍了拍手:“不磕一下,她们怎么信我快死了?”苏挽晴从袖中抽出一张纸,
展开铺在被面上。纸上墨迹未干,赫然是“肺痨重症,恐难逾月”的诊断书,
落款盖着太医院朱印。“伪造文书是杀头的罪。”沈芷寒指尖划过“肺痨”二字,
停在印章边缘,“你胆子比我想的大。”“沈家当年供我读书时,可没计较过风险。
”苏挽晴抓起她的手腕搭脉,动作利落,“脉象虚浮是装的,
但眼底血丝是真的——你几夜没睡了?”沈芷寒抽回手:“睡不着的时候,
数赵德妃派来盯梢的人更有趣。”苏挽晴从药箱底层抽出一卷绷带,
突然压低声音:“周砚拿到药材了。他托人验出乌骨藤与赤霜草的配伍,已誊录三份证词,
一份藏在大理寺卷宗夹层,一份送去了景王府。”“萧景珩怎么说?”沈芷寒接过绷带,
在腕上缠绕两圈。“他派人送来这个。”苏挽晴从发髻里摸出半枚铜钱,
断口处刻着细密纹路,“说五日后宫宴,赵国公会呈献西域贡酒——酒里掺的东西,
和你药里的同源。”沈芷寒把铜钱按进绷带结里:“他倒舍得下本。
”“他还让我问你——”苏挽晴突然拽过她的手腕,将银针扎进合谷穴,“若证据确凿,
是要赵德妃死,还是要她活着看太子倒台?”针尖刺入的瞬间,
沈芷寒眉头都没动:“我要她跪在金銮殿上,亲手撕了自己写的贤德懿旨。
”窗外传来扫帚拖地声,两人同时噤声。苏挽晴迅速收针,转身整理药箱,
嘴里提高音量:“肺痨最忌情绪起伏,姑娘若再呕血,老身也救不得了!
”门缝外脚步声顿住,又渐渐远去。沈芷寒盯着绷带上的血点,
忽然开口:“你兄长在户部当差的事,赵德妃知道吗?”苏挽晴背对着她,
手指在药瓶间停顿片刻:“上月刚调去管漕粮——怎么?
”“漕粮账册缺了三个月的损耗记录。”沈芷寒把染血的绷带塞进袖袋,
“明日我会让周砚‘偶然’发现这事。你兄长最好病一场,病到查账的钦差找不着他。
”苏挽晴猛地转身,药瓶在箱中叮当作响:“你要拿我家人做饵?”“是保他。
”沈芷寒直视她的眼睛,“赵德妃若发现账目有鬼,第一个灭口的就是经手人。
让他‘病’在太医院眼皮底下,至少我能护住。”苏挽晴抓起药箱掼在地上,
瓷瓶碎裂声惊得梁上灰尘簌簌落下。她弯腰捡拾碎片,
声音闷在臂弯里:“三年前我娘咳血等死时,是沈伯父砸了自家药铺的招牌,
换回一株百年老参——这笔债,我还到今日才算清。
”沈芷寒伸手扶她胳膊:“现在是你欠我的人情。”苏挽晴甩开她的手,
却从碎瓷堆里挑出一片完好的青瓷,塞进她掌心:“这是太医院新熬的枇杷膏,
每日卯时含服——记住,要当着送药宫女的面吐出来,说苦得咽不下。
”沈芷寒摩挲瓷片边缘:“里面加了什么?”“让你脉象更像肺痨的东西。
”苏挽晴拎起药箱走向门口,忽又回头,“对了,萧景珩让我转告——别碰宫宴上的杏仁酪,
那玩意儿解不了毒,反而会让乌骨藤发作更快。”门开合的间隙,沈芷寒瞥见院角树影晃动。
她扬声喊道:“苏医官留步!这膏药钱……”“记你账上!”苏挽晴头也不回地摆手,
“等你当上长公主,连本带利讨回来!”脚步声彻底消失后,沈芷寒掰开青瓷片。
内壁凝着琥珀色膏体,散发淡淡薄荷味。她蘸取少许抹在齿间,苦涩感立刻漫开。
这种味道她记得——前世临终前,赵德妃“好心”赏赐的安神汤里,就有同样的薄荷基底。
她将瓷片藏进床板夹层,重新躺下时,听见屋顶瓦片轻响。
这次不是监视者——瓦片移动的节奏,和昨夜萧景珩手下传递暗号的方式一模一样。
三长两短,是“计划照旧”的意思。暮色渐浓,送药宫女端着漆盘进来,
碗中药汁颜色比昨日更深。沈芷寒接过碗,突然剧烈咳嗽起来,药汁泼洒大半。
宫女慌忙擦拭,她趁机将青瓷片里的膏体混入残药,仰头灌下。“苦……”她皱眉推开碗,
“比砒霜还难喝。”宫女眼中闪过喜色,匆匆收拾退下。沈芷寒瘫在枕上,
感受着喉间灼烧感——这不是伪装。苏挽晴给的膏药确实含致幻成分,
能让人短暂呈现濒死症状。但真正让她心跳加速的,是方才在膏药底部摸到的凸起纹路。
那是沈氏旧部联络用的密文。第一笔横折代表“北境”,第二笔竖钩意为“铁骑已动”。
萧景珩不仅送来警告,更把兵权调动的消息藏在了药里。更鼓敲过二遍,
柳姑姑亲自提灯来探。沈芷寒蜷在被中,呼吸微弱如游丝。柳姑姑俯身试她鼻息,
指尖冰凉触感让她险些笑出声。“明日换虎狼药。”柳姑姑对随行太监耳语,
“务必让她在宫宴前断气。”待脚步声远去,沈芷寒掀被坐起,从发间抽出一根银簪。
簪头雕着梅花,正是她与苏挽晴约定的信物。她将簪尖插入床板缝隙,
轻轻一撬——夹层里躺着半张户籍文书,姓名栏赫然写着“苏明远”,
正是苏挽晴兄长的真名。文书末尾盖着模糊的官印,隐约可见“漕运”字样。
沈芷寒用炭笔在印痕旁添了两笔,使之变成完整的“贪墨”二字。
明日这东西就会“意外”出现在周砚案头,而赵德妃为了灭口,定会派人去太医院“探病”。
她吹熄油灯,在黑暗中数着心跳。苏挽晴赌上性命伪造病历,萧景珩冒险传递军情,
周砚即将引爆漕粮案——每个人都在往火堆里添柴,而她要做的,
是在烈焰腾空时精准投下最后一根引线。远处传来三声鸦啼,是苏挽晴约定的平安信号。
沈芷寒摸向腰间暗袋,那里藏着乌骨藤残渣与密文瓷片。复仇的棋局已铺开,
而她的第一位盟友,正带着毒药与真相穿行在宫墙阴影里。晨光初现时,
沈芷寒主动摔碎了药碗。瓷片飞溅中,她盯着宫女裙角沾染的药渍,轻声道:“告诉赵德妃,
我梦见阎王殿的生死簿上,她的名字排在我前头。”皇子疑云晨光刚漫过窗棂,
沈芷寒便咳得撕心裂肺,手帕上溅开的血点比昨日更浓。她故意让血渍沾到被面,
又将药碗推翻在地,瓷片飞溅时还夹着几声断续呻吟。柳姑姑闻声赶来,见状只冷哼一声,
命人收拾残局,转身就去回禀赵德妃。宫女换新药来时,沈芷寒没接,只靠在床头喘息,
声音沙哑:“告诉主子,我快撑不住了……让她安心。”那宫女低头应是,退下时脚步轻快,
连裙角都扬得高了些。沈芷寒盯着她背影,嘴角微不可察地扯了一下。
她知道这话会原封不动传进赵德妃耳中——正合她意。午后风起,
冷宫偏院的门被一阵急促叩响。守门太监刚拉开条缝,就被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推开。
萧景珩踏进门槛,玄色锦袍未换朝服,腰间却悬着暗麟司的令牌。他身后跟着两名侍卫,
皆低眉垂目,不发一言。“七殿下怎有空来这等地方?”沈芷寒撑起身,披衣坐直,
面色苍白如纸,唇边却挂着笑,“莫非是来送我最后一程?”萧景珩没答话,径直走到床前,
伸手扣住她手腕。指尖冰凉,力道却不容挣脱。他搭脉片刻,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
“脉象虚浮,却无死气。”他松开手,语气平淡,“装得不错。”沈芷寒收回手,
拢进袖中:“殿下若不信,不如再等几日,看我是否真能熬到宫宴那天。”“你不必熬。
”萧景珩从袖中取出一卷薄纸,展开后递到她面前,“漕粮账册缺页的事,周砚已呈报御前。
赵国公今早被召入宫,此刻还在御书房外跪着。”沈芷寒接过纸,
扫了一眼便折好收起:“殿下这是来邀功?”“不是。”萧景珩目光落在她腕间绷带上,
“苏挽晴兄长昨夜‘突发急症’,已被抬进太医院后厢。赵德妃派去的人扑了个空,
转头去找户部尚书对质,反被扣下问话。”沈芷寒轻笑:“殿下动作倒是快。”“你也不慢。
”萧景珩忽然俯身,压低声音,“乌骨藤混赤霜草,发作时脉象紊乱如痨病,
实则伤的是肝胆经络——你既知解法,为何还要喝那药?
”沈芷寒抬眼看他:“殿下既然查得这么清楚,不如猜猜我图什么?”萧景珩沉默片刻,
直起身:“你要赵德妃亲手把毒酒端到御前,让满朝文武亲眼看着她自掘坟墓。”“聪明。
”沈芷寒靠回枕上,闭目养神,“可惜殿下猜错了一点——我不只要她倒台,
我要她活着认罪,跪在百官面前,亲口承认害死了多少人。”萧景珩没再说话,
转身走向门口。临出门前,他停下脚步:“五日后宫宴,西域贡酒会由赵国公亲自呈献。
酒盏底部刻有暗纹,遇热显形——那是你父亲当年批注军饷的手记拓本。
”沈芷寒猛地睁眼:“你从哪拿到的?”“北境铁骑截下的密函。”萧景珩回头看了她一眼,
“你父亲没叛国,是赵氏伪造通敌文书,借太子之手构陷。证据我留了一份,
藏在暗麟司地窖第三格——钥匙在你手里那半枚铜钱里。”门在他身后合上,脚步声渐远。
沈芷寒攥紧铜钱,指节发白。她没想到萧景珩竟把如此重要的东西交到她手上,
更没想到他会主动揭穿赵氏阴谋。窗外传来鸟鸣,三长两短,是苏挽晴约定的信号。
沈芷寒起身下床,从床板夹层取出密文瓷片,用炭笔在背面添了一行小字:“宫宴当日,
酉时三刻,东角门。”她将瓷片重新藏好,又躺回床上,故意让呼吸变得急促。不多时,
柳姑姑果然带着两名太监进来,说是奉命查验病情。“姑娘今日气色更差了。
”柳姑姑假意叹息,伸手探她额头,“脉象也乱得很,怕是熬不过三日。”沈芷寒咳嗽两声,
虚弱道:“劳姑姑费心……我若真去了,烦请替我烧些纸钱,
就说……就说我在阴间等着赵德妃。”柳姑姑脸色一僵,强笑道:“姑娘说笑了,
德妃娘娘仁厚,怎会与你计较?”“是吗?”沈芷寒睁开眼,直勾勾盯着她,
“那姑姑可知道,她给我的药里,掺的是乌骨藤还是砒霜?”柳姑姑猛地缩回手,
后退半步:“姑娘慎言!这话若传出去,可是大不敬!”“那就别传。”沈芷寒闭上眼,
声音渐弱,“反正……我也活不久了。”柳姑姑匆匆带人离开,门关上的瞬间,
沈芷寒睁开眼,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她知道柳姑姑一定会把这话带给赵德妃——而赵德妃,
绝不会容忍一个将死之人还敢威胁她。傍晚,苏挽晴提着药箱悄悄进来,
一进门就压低声音:“你疯了?当着柳姑姑的面提乌骨藤?她要是去查药渣怎么办?
”“就是要她去查。”沈芷寒坐起身,“查出来才好——她越慌,越容易出错。
”苏挽晴咬牙:“你知不知道赵德妃已经下令,明日就要换虎狼药?那药一下肚,
神仙也救不了你!”“我知道。”沈芷寒从袖中取出铜钱,
“但萧景珩给了我这个——他说钥匙在断口纹路里。”苏挽晴接过铜钱,对着光细看,
果然发现纹路深处藏着极细的凹槽。她抬头:“他信你?”“他不信我。”沈芷寒冷笑,
“但他信我能扳倒赵氏。对他来说,我不过是颗好用的棋子——可棋子若能反客为主,
谁输谁赢,还未可知。”苏挽晴沉默片刻,从药箱底层取出一个小瓷瓶:“这是护心丹,
能暂缓毒性发作。你若真要喝虎狼药,至少先含一颗在舌下——别真把自己喝死了。
”沈芷寒接过瓷瓶,收入怀中:“多谢。”“别谢我。”苏挽晴收拾药箱,语气生硬,
“我帮你,是因为沈家对我有恩。但若你把自己玩死了,这笔债我就算不清了。”门开合间,
苏挽晴的身影消失在暮色里。沈芷寒摩挲着铜钱,忽然听见屋顶瓦片轻响——又是三长两短,
和昨夜一样。她没动,只轻声道:“殿下既然来了,何不现身一见?”瓦片声顿住,片刻后,
窗棂被轻轻推开。萧景珩跃入房中,落地无声。他没换装束,显然是一路跟来的。
“你早知道我在?”他问。“苏挽晴每次来,屋顶都有动静。”沈芷寒靠在床头,语气平静,
“第一次是试探,第二次是监视,第三次……是保护。”萧景珩没否认:“赵德妃已下令,
明日辰时送药,未时验尸。她要在宫宴前让你彻底闭嘴。”“那正好。”沈芷寒抬眼看他,
“我若‘死’在宫宴前,她的嫌疑反而洗不干净——毕竟,
谁会在大喜之日毒杀一个将死之人?除非……那人怕她说出什么。
”萧景珩走近一步:“你打算怎么演这场戏?”“很简单。”沈芷寒从枕下抽出一张纸,
递给他,“这是我拟的‘遗书’,
上面列了赵氏这些年做的所有脏事——包括毒杀嫔妃、克扣军饷、私通敌国。
我会把它藏在贴身衣物里,等‘死后’被人‘意外’发现。”萧景珩接过纸,快速扫了一遍,
眉头微皱:“证据不足,单凭这些,扳不倒她。”“所以需要殿下的配合。
”沈芷寒直视他双眼,“宫宴当日,我要你在众目睽睽之下,
拿出那份军饷手记——然后当众质问赵国公,为何伪造先父笔迹。”萧景珩沉默良久,
终于点头:“可以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”“说。”“别真喝那药。”他声音低沉,
“护心丹只能撑一时,若毒性攻心,神仙难救。”沈芷寒笑了:“殿下这是关心我?
”“不是。”萧景珩转身走向窗口,“我只是不想我的棋子,还没上场就废了。
”窗扇合拢的瞬间,沈芷寒脸上的笑意淡去。她知道萧景珩没说实话——若真只当她是棋子,
何必冒险送来军饷证据?何必提醒她别碰杏仁酪?何必深夜潜入,只为确认她是否安好?
但她没点破。现在不是谈感情的时候,复仇才是首要。至于萧景珩……等大仇得报,
她再慢慢算这笔账。更鼓敲过二遍,沈芷寒吹熄油灯,在黑暗中数着心跳。明日虎狼药一到,
她就得真正面对死亡边缘——但这一次,她不会再任人宰割。远处传来鸦啼,三声,
是苏挽晴报平安。沈芷寒摸向腰间暗袋,那里藏着乌骨藤残渣、密文瓷片,
还有萧景珩给的铜钱。萧景珩将她送回冷宫掩人耳目棋局已布,只等收官。
暗卫交锋窗棂刚合上,沈芷寒就翻身下床,把炭条塞进袖口。她没点灯,摸黑走到门边,
耳朵贴着门板听外面动静。脚步声走远了,巡逻的更夫刚敲过梆子,
整座冷宫像被掐住喉咙般安静。她拉开门栓,闪身出去,反手把门虚掩。
月光斜照在青石路上,她贴着墙根走,避开巡夜太监的灯笼光。转过三道回廊,
绕过两处岗哨,她在假山后蹲下,等一队侍卫走过才继续前行。尚书府就在宫墙外第三条街,
她前世死前偷看过赵德妃藏密信的地方——书房东墙后头有个暗格,
钥匙在赵尚书贴身玉佩里。她翻墙进府时没惊动狗,落地轻得像片叶子。
府内守卫比她预想的松,只在主院设了岗。她贴着屋檐阴影走,绕到书房窗下,
指尖刚搭上窗框,背后风声骤起。箭矢破空而来,她侧身躲开第一支,
第二支擦着耳垂钉进窗框。第三支直冲心口,她退无可退,脊背抵住墙壁,
眼看箭尖逼近——一道黑影从屋顶跃下,横挡在她身前。箭头扎进他左肩,闷哼一声,
人却没倒。他反手拔出短刀,甩向屋顶暗处,一声惨叫后有人坠地。他转身看她,
眼神冷得发硬,右手一扬,一块铁牌砸进她怀里。“七殿下说,你的命现在归他管。
”沈芷寒低头看那令牌,正面刻麒麟踏云,背面一个“景”字。她抬头想问,
那人已捂着伤口跃上房梁,几个起落消失在夜色里。屋顶传来几声打斗闷响,很快归于寂静。
她攥紧令牌,转身踹开书房窗,翻身进去。屋里没点灯,她摸到书案后,
手指沿东墙砖缝摸索。第三块砖松动,她抠出来,里面是个小匣子。打开一看,是半本账册,
记着赵国公私调军粮的事。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,她迅速把账册塞进怀里,闪身躲到屏风后。
门被推开,烛光晃进来,赵尚书的声音带着醉意:“……明日早朝,务必让周砚闭嘴。
他查的那些旧案,一件都不能翻。”另一人低声应:“可大理寺那边……”“让他查,
查到死也查不出东西。”赵尚书冷笑,“沈家那丫头还关在冷宫?派人盯着,
别让她活过月底。”脚步声渐远,门重新关上。沈芷寒等了片刻,从后窗翻出,原路返回。
快到冷宫时,她拐进御花园假山群,在最深处的石洞里停下。洞壁潮湿,她掏出账册,
借着月光快速翻看。每一页都盖着户部大印,经手人名字被墨涂掉,
但笔迹她认得——是太子亲信。她撕下关键几页,塞进鞋底夹层,其余烧成灰。
火苗舔舐纸页时,洞口传来轻响。她猛地转身,短刀抵在胸前。“是我。
”苏挽晴提着药箱钻进来,脸上沾着泥,“你疯了?大半夜跑尚书府?
我差点被巡夜的当成刺客抓起来。”沈芷寒收起刀: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?
”“萧景珩的人找上我,说你今晚有动作,让我来接应。”苏挽晴压低声音,
“他派来的暗卫受伤不轻,血滴了一路。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人?”“赵尚书养的死士。
”沈芷寒把令牌递过去,“这个能保我们多久?”苏挽晴接过看了眼,
脸色变了:“暗麟司的通行令?他居然把这个给你……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从今往后,
七皇子府的人见你如见主子,连赵德妃都不敢明着动你。”“我不需要他保。
”沈芷寒拿回令牌,“我要的是他手里的北境军报,还有暗麟司三年前查赵国公贪污的卷宗。
”苏挽晴叹气:“你当他是钱庄掌柜?要什么给什么?”“他想要赵德妃的命。
”沈芷寒蹲下身,用炭条在石壁上画了个叉,“我手里有她毒杀先皇后的证据,
还有太子买通边关守将私贩军械的账本。这些够不够换他出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