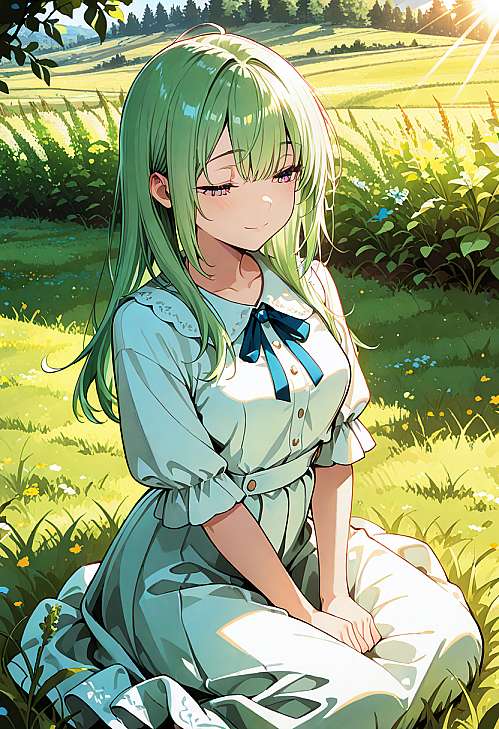箱子被抬进卧房时,沉得像口棺材。我的手指刚碰到那铜锁扣,门就被推开了。
程砚穿着朝服站在门口,天青色的云雁补子映着他毫无表情的脸。
他身后跟着管家和两个小厮,手里捧着大大小小的锦盒。“夫人。
”他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,“陛下今日赏赐了些江南进贡的丝绸,我已吩咐送去库房。
这几盒是给你挑的。”我没回头,指尖还停在那冰凉的铜扣上。“这箱子,
”我的声音有些哑,“放哪儿?”屋子里静了一瞬。程砚走到我身后,
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墨香,混杂着今日在宫中沾染的檀香气息。他的影子投在箱子上,
正好盖住我按着锁扣的手。“先放这儿吧。”他说,“过几日我让张叔收拾。
”“里头是什么?”“一些旧物。”他答得极快,快到不像是在回答,倒像是在打断,
“不紧要的。”我转过身,抬眼看他。十三年了,这张脸我看了十三年。
从新婚那夜的少年郎,到如今朝中人人称颂的程侍郎。眉宇间那点青涩早已磨平,
只剩下一副妥帖得体的官场面孔。“不紧要的,”我慢慢重复,
“怎么还特意让人从老宅抬回来?”程砚避开了我的目光。他走向窗边的茶案,
自顾自倒了杯茶。茶盏碰到桌面的声音清脆得刺耳。“母亲说老宅要修缮,
这些零碎物件总得有个去处。”他啜了口茶,“你若不喜,明日便让张叔搬去偏房。
”我没接话。屋子里又静下来,只剩窗外雨打芭蕉的声音。春末的雨下得绵密,
把天光都染成了灰青色。两个小厮放下锦盒便退了出去,管家站在门口,
欲言又止地看了眼程砚。“还有事?”我问。管家垂下眼:“回夫人,老夫人那边传话,
说表小姐明日要来府上小住。”我笑了。很轻的一声笑,轻得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。
“哪个表小姐?”“是……是江南苏家的三小姐,苏婉清。”管家声音越来越低,
“老夫人说,苏小姐今年十六,想来京城看看,顺便……寻个好人家。
”程砚放下茶盏:“知道了。你去安排住处,就安排在西跨院的听雨轩吧。”管家应声退下,
房门在他身后合上。我走到窗前,看雨丝斜斜地飘进来,打湿了窗台上的那盆兰草。
“苏婉清。”我念着这个名字,“我记得她。三年前江南水灾,苏家来投奔,
她母亲带着她在程府住了三个月。”“是。”程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“那时她才十三岁。
”“今年十六了。”我转过身子,背靠着窗沿,“好年纪。”程砚终于看向我,
眉头微蹙:“你什么意思?”“没什么意思。”我抬手理了理鬓发,“十六岁,
正是该说亲的时候。母亲替她张罗,也是应当的。”“你不要多想。”“我想什么了?
”我歪着头看他,“程侍郎,你说说,我该想什么?”程砚站起身。
他的身形在昏暗的室内显得有些高,官袍的下摆拂过地面,发出细微的窸窣声。
“苏婉清只是来小住,寻个好人家嫁了便走。”他走到我面前,停下,
“你何必用这种语气说话?”“我哪种语气?”“阴阳怪气的语气。”我又笑了,
这次笑出了声。“程砚,”我叫他的名字,十三年了,我很少这样连名带姓地叫他,
“你是不是觉得,我该欢天喜地地替你表妹张罗婚事?是不是觉得,
我该像个贤惠大度的正室夫人,把她留在府里住上三五个月,日日陪她逛铺子选衣料,
再动用我所有的人脉,给她找个高门大户?”程砚的脸沉了下来。“我没有这么说。
”“可你这么想了。”我迎上他的目光,“从你让管家安排听雨轩的时候,你就这么想了。
听雨轩挨着你的书房,最清静,也最方便。方便什么?方便你这位当朝侍郎,
亲自教导你那十六岁的表妹?”“林晚!”程砚的声音陡然拔高,“你胡说什么!
”“我胡说?”我向前走了一步,几乎贴上他的胸口,“三年前她来的时候,
你手把手教她写字,记得吗?你说她字写得不好,你说她手腕不稳。你说,砚哥哥教你。
”程砚后退了一步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,
但很快被怒意掩盖:“那不过是长辈对晚辈的教导!”“教导?”我笑得更厉害了,“是啊,
教导。教导到深更半夜,教导到她靠在书案边睡着了,你亲自抱她回房?
”“你——”“我怎么知道的?”我打断他,“因为那天晚上我就在书房外。
我亲手炖了参汤给你送去,我看见你抱着她,她的手环着你的脖子,脸贴在你胸前。
她睡得那么香,香到连我推门的声音都没听见。”雨声更大了。哗啦啦地砸在屋檐上,
像要把整个春天都冲走。程砚的脸色从红转白,又从白转青。他的嘴唇动了动,
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。“你没看见我,”我接着说,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惊讶,
“因为你背对着门。你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榻上,还替她掖了掖被角。
你站在那儿看了她很久,久到我手里的汤都凉透了。”“所以这三年来,”程砚终于开口,
声音嘶哑,“你一直——”“一直装不知道。”我替他补完,“是啊,我装不知道。
我装了三年的贤惠夫人,装了三年的体贴妻子。我在母亲面前夸你顾家,
在同僚夫人面前夸你体贴。我甚至在你生辰那夜,主动提起该纳个妾了。”我顿了顿,
指甲掐进掌心。“可你是怎么回我的?你说,你有我就够了。你说,
你不愿旁人来分走我们之间的情分。”程砚闭上了眼睛。“现在呢?”我问,
“现在苏婉清十六岁了,母亲说她该寻个好人家了。可你说说,程砚,什么样的人家,
才算好人家?”他睁开眼,眼里布满了血丝。“晚儿,”他叫我的乳名,声音软下来,
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婉清她那时还小,我……”“她不小了。”我打断他,
“她当时十三岁,不是三岁。她懂得靠在男人怀里装睡,懂得把手环在男人脖子上。
她甚至懂得,在我进门时故意把簪子掉在地上,让你弯下腰去捡。
”程砚猛地抬头:“什么簪子?”“一支白玉簪子。”我慢慢地说,“掉在你脚边。
你弯腰去捡的时候,她的手‘不小心’扶住了你的肩。那一扶,整个人都快贴到你身上去了。
”“你为什么不早说?”“早说?”我看着他,“早说你信吗?你会信你的晚儿,
还是信你那楚楚可怜的表妹?”程砚说不出话了。他站在那儿,像一尊突然被掏空的雕像。
朝服还穿在身上,补子上的云雁栩栩如生,可他人已经垮了。我走到箱子边,重新蹲下身。
铜锁扣在我手指下冰凉刺骨。“这箱子,”我说,“我自己收拾。”“晚儿……”“程侍郎。
”我头也不抬,“你该去书房了。今日的奏折还没批完吧?陛下最近器重你,
可别耽误了正事。”身后传来长长的吸气声。然后是脚步声,一步一步,沉重地走向门口。
门开了,又合上。我跪坐在箱子前,盯着那铜锁扣看了很久。直到膝盖开始发麻,
直到窗外的雨渐渐小了,天色彻底暗下来。我找来一把小锤,轻轻敲开了锁扣。
箱盖掀开的瞬间,灰尘扬起来,在昏暗的光线里飞舞。我捂住口鼻,等尘埃落定,
才看清里面的东西。最上面是一件红色嫁衣。十三年前的嫁衣,是我娘亲手绣的。
金线绣的凤凰已经黯淡了,可那大红的底色依然刺眼。我伸手摸了摸,绸缎冰凉,
像死人的皮肤。嫁衣下面是一摞书信。全都是程砚写给我的。从我们定亲开始,
到他高中探花,到他入朝为官。最早的那些信纸上,字迹还有些青涩,写着“一日不见,
如隔三秋”,写着“愿得一人心,白首不相离”。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。
是六年前他外放江南时写的。信上说,江南多雨,他想念京城干爽的秋天,
更想念我炖的鸡汤。信末写:等我回来,定不负卿。我没哭。我只是把信放回去,
继续往下翻。
嫁衣、书信、几件我早年绣的帕子、一支断了的玉簪——是婚后第一年他送我的生辰礼,
被我失手摔断了,他一直说要找人修补,却再也没提过。再往下,是一个紫檀木的小盒子。
我把它拿出来,放在膝上。盒子没有锁,一掀就开。里面是一张纸。折叠得很整齐,
纸张已经泛黄,边角有些磨损。我慢慢地、慢慢地展开它。休书。两个字映入眼帘时,
我的呼吸停了一瞬。这是一封休书。字迹是程砚的,但比现在的字迹要稚嫩些。
日期是十年前,嘉和七年,三月初九。正是我小产后的第三日。我跪在冰冷的砖地上,
一遍遍读着上面的字:“程门林氏,七出有其三。无子,善妒,口多言。今立此休书,
任其改嫁,永无争执。恐后无凭,立此文约为照。”下面有他的签名,还有手印。红得刺目。
我的手指开始发抖,纸在指尖哗啦作响。我闭上眼,又睁开,那些字还在那里,一笔一画,
清清楚楚。无子。善妒。口多言。我笑了起来,开始是低笑,后来变成大笑,
笑得眼泪都出来了,笑得整个人伏在箱子上,肩膀不停地颤抖。十年了。
这封休书在箱底躺了十年。而我,在他身边又做了十年的程夫人。替他打理家事,
替他孝敬母亲,替他周旋于各府夫人之间,替他维持着“夫妻和睦”的假象。
窗外的雨彻底停了。夜色浓得化不开,房间里没有点灯,只有从窗缝透进来的一点月光,
冷冷地照在那张纸上。我把休书重新折好,放回盒子。然后我站起身,腿麻得几乎站不稳,
扶着箱子缓了好一会儿。脚步声在门外响起,由远及近。不是程砚的步子。
他的步子我听得出来,沉稳,均匀,每一步都丈量好了似的。这是小跑的步子,细碎而急促。
接着是敲门声,很轻,带着试探:“夫人?夫人您在里面吗?”是春桃,我的贴身丫鬟。
“什么事?”我开口,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静。“表小姐……苏小姐到了。
”春桃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老夫人让您去前厅见见。”我走到门边,但没有开门。
“告诉老夫人,我身子不适,已经歇下了。”“可是……”春桃有些犹豫,
“表小姐特意带了礼物,说一定要亲手交给您。”我沉默了片刻。“什么礼物?
”“是一对玉镯。苏小姐说,是江南最好的籽玉打的,她母亲嘱咐了,一定要送给表嫂。
”我笑了。这对玉镯我听说过。三年前苏夫人来的时候,就戴在手上,成色极好,
水头足得能滴出来。当时她还说,这是苏家祖传的,要留给婉清当嫁妆。现在,
这“嫁妆”要送给我了。“收下吧。”我说,“替我谢谢表小姐。”“夫人不见见吗?
”春桃的声音更低了,“表小姐一来就往书房去了,
说是给表哥带了江南的明前茶……”我的手指按在门框上,用力到骨节发白。“春桃。
”“奴婢在。”“去书房。”我一字一句地说,“告诉老爷,
就说我说的——表小姐远道而来,一路辛苦,不该再劳烦她亲自奉茶。
让他送表小姐回听雨轩,早点歇着。”门外静了一瞬。然后春桃应了声“是”,
脚步声匆匆远去。我背靠着门板,慢慢滑坐到地上。月光从窗缝漏进来,
正好照在那口箱子上。铜锁扣在月光下泛着冷光,像一只眼睛,静静地看着我。我看着它,
看了很久。然后我站起身,走到妆台前,点燃了蜡烛。铜镜里映出一张脸。三十三岁的脸,
眼角已经有了细纹,嘴唇抿得太紧,显得刻薄。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,亮得像两簇火,
在烛光里跳动。我拿起梳子,慢慢地梳头。一下,两下,三下。梳齿刮过头皮,
带来微微的刺痛。这痛让我清醒,清醒地意识到:那封休书烂在箱底十年。而有些东西,
烂在心里,也该挖出来了。(未完待续)蜡烛的火苗晃了晃,在铜镜里拖出摇曳的影子。
我将头发一丝不苟地绾好,选了支素银簪子固定。平日里见客的那些金钗珠翠,
此刻看着都扎眼。只有这支簪子,是母亲在我出嫁前给的,她说银器最衬人,清白,硬气。
前厅的喧闹隐隐约约传过来,丝竹声、说笑声,混在潮湿的夜风里。听雨轩离我的院子不远,
那里种了许多芭蕉,下雨时声音格外清晰。程砚喜欢在那里读书,说清净。此刻,
那里的灯火想必是暖的,明前茶的香气也一定飘出来了。春桃回来得很快,脚步声停在门外,
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喘息。“夫人,话带到了。”她隔着门轻声说,
“老爷他……他让奴婢先回来伺候您歇息。表小姐……老爷亲自送回去了。”我对着镜子,
将鬓边一丝碎发抿好。“他怎么说?”“老爷没多说什么,只点了点头,说‘知道了’。
”春桃顿了顿,声音更轻了些,“不过,奴婢去的时候,表小姐正给老爷斟茶,
那茶盏……是老爷平日最爱的雨过天青盏。”我的心像是被那冰凉的瓷盏轻轻碰了一下,
不重,却闷闷地疼。那只茶盏,还是我们新婚时,我跑遍大半个京城寻来的,
只因他说过喜爱那个颜色。这些年,他一直用着。“知道了。”我的声音依旧平静,
“你去歇着吧,今晚不用守夜。”“夫人……”春桃欲言又止。“去吧。”门外静了。
我吹灭了蜡烛,却没有回到床上。月光清冷,我倚着窗,看向听雨轩的方向。
那里的一扇窗格外明亮,窗纸上映出两个模糊的影子,一个挺拔,一个窈窕,似乎靠得很近。
夜色里,有什么东西在悄悄碎裂。不是响亮的破碎,而是那种缓慢的、细微的皲裂声,
从心底最深处蔓延上来。不知过了多久,那扇明亮的窗终于暗了下去。
整个程府沉入更深的寂静,只有更夫敲梆子的声音,一下,又一下,空洞地回荡。我转身,
没有再看那口箱子,而是打开了衣橱最深处的一个小抽屉。里面没有珠宝,只有几封旧信,
边角已经磨损发黄。最下面,压着一块玉佩,不是名贵的材质,甚至有些粗糙,
上面刻着一个简单的“宁”字。手指抚过冰凉的玉佩,许多年前的声音仿佛穿过时光,
又一次在耳边响起,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朗和笑意:“阿禾,等我回来,
一定用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”那是林衍之,我的宁哥哥。出征前夜,他翻墙进来,
将这玉佩塞进我手里。后来,八抬大轿是来了,抬我进的却是程家的门。
林衍之死在了北境的战报里,程砚奉旨娶了我这个“功臣遗孤”。十年了。
程砚心里装着白月光般的苏婉清,我心底何尝不是埋着一道旧伤疤。我们相敬如“冰”,
各自守着各自的废墟,还要在人前扮出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我将玉佩紧紧攥在掌心,
坚硬的棱角硌得生疼。这块玉佩和箱底那封休书一样,
都是不该存在、却又实实在在横在那里的东西。窗外,远远传来一声悠长的猫叫,凄清得很。
明天,太阳照常升起。苏婉清会以“客居”之名,名正言顺地住进听雨轩。
老夫人的嘘寒问暖,下人们的窃窃私语,各府夫人探究的目光……所有这些,
都会像潮水一样涌来。而我这个“程夫人”,是继续站在潮水中,维持那片看似平静的水面,
还是……亲手搅动这潭死水?指尖的疼痛愈发清晰。我松开手,将玉佩放回原处,
关上了抽屉。有些东西,埋得太久,或许真的到了该见见天日的时候了。
哪怕撕开时会鲜血淋漓,也好过任由它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腐烂,最终连自己都一并吞噬。
夜还很长。我坐回妆台前,在黑暗里,静静等待着黎明。窗外传来第一声鸡鸣时,
我仍坐在妆台前。铜镜里映着一张模糊的脸,眼下的青影连脂粉都难以遮掩。一夜未眠,
心头那点闷疼没有散去,反而凝成了某种坚硬的东西。起身时腿脚有些发麻。
我扶住妆台站稳,唤春桃进来梳洗。“夫人脸色不大好。”春桃小心翼翼地说,
梳头的手格外轻柔,“可要多敷些粉?”“不必。”我盯着镜中自己,“就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