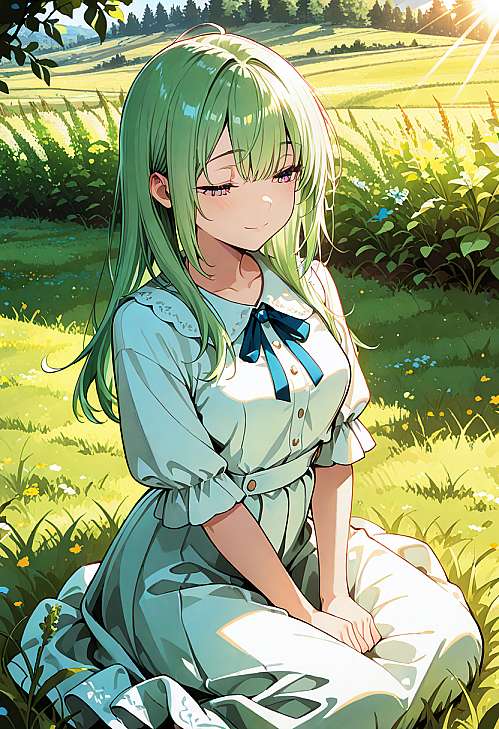花轿落地的时候,鞭炮没响。迎亲的婆子连杯茶都没备,领着我从侧门进了王府。
正门大开着,红绸挂了满院。那是三年前,姐姐嫁进来时用的。至今没摘。“侧妃娘娘,
您的院子在西跨院,奴婢带您过去。”婆子连正眼都不给我一个。我提着裙摆,跟在她身后,
穿过三道回廊。西跨院的门漆都裂了,院里杂草齐膝。“这就是我的院子?
”“侧妃娘娘见谅,府里近来事多,还没来得及收拾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,嘴角是翘的。
我没说话。把嫁妆箱子一只只搬进去,亲手拔了院里的草。从侯府到王府,我走了十六年。
不急。1、第二天一早,姐姐就来了。她穿着正红色的褙子,头上戴着赤金点翠的凤钗,
身后跟了六个丫鬟。排场摆得足足的,连进门的步子都带着节拍,生怕旁人不知道她是正妃。
“妹妹,你这院子也太寒酸了。”她坐在唯一一把完好的椅子上,拿帕子擦了擦扶手,
皱着眉。“早知道你要来,我该让人提前收拾收拾。”“劳姐姐挂心了。”我站着,
给她倒茶。茶是我自己带的,杯子是嫁妆里的。王府连茶叶都没给我备。
姐姐端起杯子抿了一口,忽然笑了。“这茶不错。是娘给你的?”她嘴里的“娘”,
是嫡母宋氏。宋氏给我备的嫁妆里确实有茶,不过是三年前的陈茶,受了潮,
泡出来一股霉味。我手里这罐,是我自己攒银子买的。“是。”我笑着答。
没必要在这种事上争。“妹妹,”姐姐放下杯子,语气忽然变了,
“你知道王爷为什么娶你吗?”我没接话。“宫里贵妃娘娘发的话。
她觉得我一个人管不好这么大的王府,要给王爷再添一房。”她看着我,眼神居高临下。
“说白了,你就是来帮我干活的。”我垂着眼,没反驳。她要这么想,随她。“所以,
”她站起来,拍了拍裙子上并不存在的灰,“王府的中馈,我会分一部分给你。
采买、浆洗、灶房,这些你管。其余的,不必操心。”采买、浆洗、灶房。
全是最累、最琐碎、最容易出错的活。出了差池是我的责任,办好了是她调度有方。
“多谢姐姐信任。”我行了个礼,目送她带着六个丫鬟浩浩荡荡地走了。翠屏关上门,
急得直跺脚。“娘娘!她分明是把您当管事婆子使!”翠屏在人前叫我“娘娘”,
关起门来还是改不了口,叫“小姐”。我没纠正过。在这座府里,
她是唯一还把我当小姐看的人。“她给的。”我坐下来,拿出随身带的账簿,“接了,
才有机会看王府的账。”翠屏一愣。“你觉得,一个连茶叶都不给侧妃备的王府,
账目能干净到哪去?”2、接手采买、浆洗、灶房三项,我用了七天摸清门道。王府的账,
果然不干净。不是小打小闹。灶房每月报上来的菜钱,够养活半条街。采买的绸缎布匹,
价格比外头贵出三成。浆洗房的皂角、澡豆,一个月用掉的量够洗一年。我没声张,
一笔一笔记在自己的小账本上。第十天,灶房管事周嬷嬷来找我。“侧妃娘娘,
这个月的菜钱该批了。”她递过来一张单子,上面列着各项开支,
末尾写着:合计纹银四十二两。我接过来看了一遍。“周嬷嬷,府里主子加上下人,
一共多少口人?”“回娘娘,满打满算,一百二十三口。”“一百二十三口人,
一个月菜钱四十二两?”“是。”她脸上的笑纹丝不动,“往年都是这个数,
正妃娘娘都批的。”我点了点头,提笔。她眼睛亮了一下。我在单子上画了个圈。
不是批准的红圈。是把“四十二两”三个字圈出来,
旁边写了一行小字:“请附各项明细及市价参照。”周嬷嬷的笑僵了。
“这……往年都不需要明细的。”“往年是往年。”我把单子推回去,“我接手了,
就按我的规矩来。以后所有报账,都要附明细和市价。差价超过一成的,另附说明。
”她攥着单子站了半天,走了。翠屏小声说:“小姐,她是正妃娘娘的人。”“我知道。
”“那您还——”“她是正妃的人,吃的是王府的银子。”我把账本收好,“这些银子,
最后都要王爷出。”三天后,周嬷嬷递了新单子来。明细列得密密麻麻,合计:二十六两。
一个月,少了十六两。我什么都没说,批了。但我知道,这二十六两里,仍然有水分。不急。
一步一步来。3、查账查了半个月,我发现了一笔更大的。王府名下有三间铺子,
一间绸缎庄,一间粮铺,一间药铺。账面上写的是年入八百两,
实际上我让翠屏的弟弟翠松去打听了,三间铺子至少年入一千五百两。七百两的差额,
去了哪里?我翻遍了账簿,
发现每笔“损耗”“折旧”“维修”都走的同一个人——王府外管事赵全。而赵全,
是姐姐的陪嫁。这就说通了。姐姐嫁进来三年,把王府的银子流水一样往外搬。
我若是个安分的侧妃,这些账永远不会有人查。我还没想好怎么用这些东西。
但有人替我做了决定。那天下午,王爷身边的长随李德来了西跨院。“侧妃娘娘,
王爷请您过去正堂说话。”正堂里,王爷坐在上首。他穿着一身石青色的常服,
手里捏着一本账册。是我接手之后重新整理的那本。“本王听说,
你把灶房的月支减了十六两?”我心里一紧。不知道是谁告的状。但意料之中。“回王爷,
不是减了,是核实了。”“哦?”“灶房报上来的菜钱,
妾身按实际人口和市价重新核算了一遍。原来的四十二两里,有十六两对不上明细。
周嬷嬷自己也认了,重新报了二十六两。”王爷翻了翻账册。“你在侯府学过管账?
”“妾身的生母在世时,管过侯府的灶房。妾身从小跟着看,学了些皮毛。”这话是真的。
我娘是侯府的妾室,没名没分,但灶房的账一笔不差。后来她病死了,灶房的账就乱了,
嫡母宋氏接手,亏空反而越来越大。没人提过我娘的好。也没人在意她是怎么死的。
王爷看了我一会儿,把账册放下了。“王府的账,你继续查。每月结果报给李德。”我行礼。
“妾身领命。”出了正堂,我的手心全是汗。不是怕。是知道,从这一刻起,
我不再是姐姐嘴里那个“来帮忙干活的”。王爷给了我一把尺子。我要量的,是整个王府。
4、王爷让我查账的事,姐姐第二天就知道了。她没来找我。
她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——请嫡母宋氏来了。宋氏到王府那天,排场不小。两顶暖轿,
八个随从,还带了四箱“给两个女儿的补品”。姐姐亲自到门口迎接,
母女俩手挽着手进了正院,亲热得不得了。我在西跨院听到消息,没动。宋氏不会来看我的。
果然,从午时到酉时,没有人来请我。酉时末,翠屏从外头打听回来,脸色不好看。“小姐,
宋夫人在正妃娘娘那儿说了半天的话。奴婢打听到,她跟正妃娘娘说,让您别揽太多事,
免得'越了规矩'。”“还说什么?”“还说……”翠屏咬了咬嘴唇,
“还说小姐您不懂王府的规矩,查账什么的,容易得罪人,让正妃娘娘管着您点。”我笑了。
宋氏这个人,我太了解了。她表面上是来“劝”我,实际上是在给姐姐撑腰。她最怕的,
是我在王府站稳脚跟。因为她心里清楚——当年我娘是怎么死的。“翠屏,
宋夫人带来的四箱补品,给正妃那边送了几箱?”“三箱。给您这边送来一箱。
”“打开看看。”翠屏打开箱子,里面是几包干枣、一盒枸杞、两罐成色一般的燕窝。
她翻了翻,忽然“咦”了一声。“小姐,箱底有封信。”我拆开。信是宋氏写的,
寥寥几行:“到了王府,安分守己,莫要多事。你的身份,自己心里有数。
”我把信放在烛火上,看着它一点点烧成灰。我的身份?庶女,妾生的,没人要的。
在侯府十六年,她就是用这句话压了我十六年。可她忘了一件事。我不在侯府了。
5、宋氏走后第三天,姐姐出手了。不是冲我。是冲王爷。她在正院摆了一桌酒席,
请王爷过去用晚膳。席间她哭了,说自己嫁进来三年,操持王府上上下下,
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如今来了个侧妃,王爷就把账交给她查,让她这个正妃的脸往哪搁。
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,我正在核对绸缎庄的出货记录。“小姐,您不去解释一下?
”翠屏急了。“解释什么?”“正妃娘娘在王爷面前哭呢!万一王爷心软——”“她哭,
是因为她慌了。”我头也没抬,“王爷要是心软,当初就不会让我查账。”我赌的,
是王爷这个人。靖安王赵恪,今年二十七,先帝第五子,当今圣上的异母弟。
他的封号是“靖安”,意思是“安定一方”。他的封地在西北,那是苦寒之地,年年打仗。
三年前他被召回京城,圣上让他挂了个闲职,明面上是恩宠,实际上是把他困在京城。
这样的人,要的不是一个会哭的正妃。他要的是一个能帮他的人。果然,第二天,
李德又来了。“侧妃娘娘,王爷说,账照查,不必理会旁人。另外,王爷让我把这个给您。
”他递过来一把钥匙。“这是库房的钥匙。王爷说,从今日起,库房也归您管。”库房。
那是王府的命脉。金银、地契、田产、首饰,全在里头。姐姐管了三年都没拿到的东西,
王爷直接交给了我。翠屏接过钥匙的时候,手都在抖。“小姐……”“收好。
”我把钥匙挂在腰间,“从今天起,王府的每一两银子,我都要知道去向。”当天晚上,
姐姐身边的大丫鬟碧桃来了西跨院。“侧妃娘娘,我们正妃娘娘请您明日去正院,
说有事商量。”语气不善。我笑了笑。“替我谢过姐姐,明日一早就到。”碧桃走后,
翠屏问我:“小姐,去吗?”“去。”“可是——”“她找我商量,
说明她还想体面地要回库房的权。”我解开发髻,“如果她不找我,直接去王爷那里闹,
那才麻烦。”“可她要是为难您呢?”“她当然会为难我。”我看着铜镜里的自己。
十六年了,我还怕为难?6、正院的门槛,比我想象的高。不是真的高。
是姐姐故意在门口摆了一架紫檀木的屏风,我进门时得侧着身子绕过去。小手段。
让你一进门就矮一截。姐姐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,身边站着碧桃和另外三个丫鬟。
桌上摆了茶点,但只有一套杯盏。意思很明白:没你的份。“妹妹来了。”她笑着,
语气比上次冷了三分。“姐姐。”我行了个礼。“坐。”我看了一圈,没有多余的椅子。
碧桃搬了个小杌子过来,放在姐姐的斜下方。我没坐。“站着说吧,不耽误姐姐的时间。
”姐姐的眉毛挑了一下,没说什么。“妹妹,你接手库房的事,我听说了。
”“是王爷的意思。”“王爷的意思,”她重复了一遍,语气玩味,“妹妹进府不过一个月,
倒是比我三年的情分还管用。”这话有刺。我没接。“妹妹,我说句实在话。”她端起茶,
吹了吹,“库房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里头的东西,哪些是王爷的,
哪些是我带来的嫁妆,哪些是宫里赐下来的,哪些是祖上传下来的——你分得清吗?
”“分不清的,我会请教姐姐。”“请教我?”她笑了,“你是来请教的,还是来查我的?
”话说到这份上了。“姐姐多心了。”我看着她,“我查的是账,不是人。”“账是人做的。
”“对。所以账有问题,人也脱不了干系。”她的手紧了一下,茶杯磕在托盘上,
发出一声脆响。“方锦书,你别忘了你的身份。”她不叫我“妹妹”了。“你是侧妃,
我是正妃。这个王府,我才是当家主母。”我没退。“姐姐说得对,您是正妃。
可库房钥匙是王爷给我的。姐姐若觉得不妥,大可去跟王爷说。”她的脸色变了。她去不了。
昨晚她已经哭过一次了,再去闹,就不是撒娇,是泼妇了。僵持了一会儿,
她忽然换了一副脸色。“罢了。妹妹能干,我省心。”她站起来,理了理袖口。
“不过妹妹记着,库房里有三口紫檀箱子,是我的嫁妆。你查账归查账,别碰我的东西。
”“自然。”我行礼退了出来。回到西跨院,翠屏迎上来。“小姐,怎么样?”“她在怕。
”“怕什么?”“怕我打开那三口紫檀箱子。”翠屏一愣。“她特意嘱咐我别碰,
说明那里头,有不能让人看见的东西。”7、我没有急着去碰那三口箱子。
我先做了另一件事——把王府上下一百二十三口人的名册重新理了一遍。
名册是姐姐管的时候造的,我拿到手一对,发现了问题。名册上写的是一百二十三人,
可我让翠屏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数过去,实际只有一百零七人。多出来的十六个人,在哪里?
我查了三天。答案是:不在。这十六个人,有的是早就被打发走的,有的压根不存在。
但他们的月钱,每月照领不误。谁在领?赵全。又是赵全。十六个人,
每人月钱从一两到三两不等,一个月就是三十多两。一年下来,将近四百两。
加上铺子的七百两差额,灶房的水分,零零碎碎的——姐姐每年从王府搬走的银子,
至少一千二百两。三年,就是三千六百两。这个数字,够在京城买两座宅子了。
我把这些整理成册,但没有交给李德。不是时候。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更重要的事。这些银子,
不全是姐姐自己花的。赵全每个月都会从京城出去一趟,去一个叫“清河庄”的地方。
那是宋氏的陪嫁田庄。银子是从王府搬出去,送进了侯府。姐姐不是在中饱私囊,
她是在给嫡母输血。宋氏让姐姐嫁进王府,不只是为了攀高枝。她是在王府插了一根管子,
往侯府抽银子。而我被送进来当侧妃,原本的用意,
是给姐姐当挡箭牌——万一哪天账被查了,顶罪的是我。想通这一层,我后背冒了冷汗。
好一个宋氏。好一个“安分守己,莫要多事”。她是怕我多事吗?她是怕我发现。
8、第二个月末,王爷召我去正堂议事。这次不是单独见面。姐姐也在。
“绸缎庄上个月的账,你查过了?”王爷翻着我呈上去的报表。“回王爷,查过了。
绸缎庄上月实际进项是一百四十七两,报上来的是八十两。差额六十七两。
”姐姐的脸微微一变。她没想到我会当着她的面说。“差额的去向?
”“走的是外管事赵全的账。妾身查了他经手的所有条目,发现类似情况不止绸缎庄一处。
粮铺、药铺、月钱名册,都有出入。”“你的意思是,赵全贪了?”姐姐忽然开口了。
“王爷,赵全是我的陪嫁。他跟了我十多年,做事一向妥当。妹妹刚来不久,
怕是不了解情况,会不会是算错了?”她看向我,目光像刀。“姐姐说得对,我是可能算错。
”我低着头,“所以妾身把所有原始凭据都整理在这里了。”我递上一沓纸。“每一笔差额,
都标了出处、日期和经手人。若是妾身算错了,请王爷和姐姐指正。”王爷接过去翻了几页,
没说话。姐姐坐不住了。“王爷,账目的事,容我回去核实一下。赵全跟了我多年,
我不相信他会——”“不必了。”王爷合上凭据,语气平淡。“赵全先关起来,
账目交大理寺的人查。”“王爷!”姐姐站了起来。“正妃。”王爷抬眼看她,“你是想说,
查你的陪嫁是不给你面子?”姐姐愣住了。“本王的面子,也不是这么丢的。”他站起来,
把凭据递给李德。“三年了,本王的王府,被人当了提线木偶。正妃,你该给本王一个交代。
”他没有说“你贪了”。但每个字都指向同一个意思。姐姐的嘴唇在发抖。
她看了我一眼——那个眼神,我太熟悉了。小时候我不小心弄脏了她的裙子,
她就是这么看我的。只不过那时候,她看完之后可以打我。现在不行了。她扶着椅背,
深吸一口气。“王爷,妾身……管教不力,愿意认罚。但赵全的事,妾身确实不知情。
”不知情?三年,每个月赵全都往清河庄送银子,她不知情?我没拆穿。不是时候。
银子的最终去向——宋氏那里——这张牌,我还得留着。王爷看了她半晌,
说了一句话:“正妃,从今日起,中馈全权交由侧妃。你好好养着,别操心了。
”这句话比罚跪还重。“别操心了”——你不配操心了。姐姐走出正堂的时候,脚步是飘的。
9、赵全关进柴房的当晚,姐姐的院子亮了一夜的灯。第二天一早,碧桃来了西跨院。
这次她的态度完全不同。“侧妃娘娘,我们娘娘身子不舒服,想请您过去坐坐。”我去了。
姐姐靠在床头,脸上没有脂粉,眼圈是红的。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“锦书。
”她叫的是我的名字,不是“妹妹”,也不是“方锦书”。“姐姐。”“你查到了多少?
”我沉默了一会儿。“姐姐想听实话?”“说。”“赵全经手的账,
从三年前姐姐进府就开始了。铺子、灶房、月钱,加在一起,三年总共约三千六百两。
”她闭上了眼睛。“你知道银子去了哪儿?”“清河庄。”她猛地睁开眼。
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?”“半个月前。”“你没告诉王爷?”“没有。”她看着我,
眼里的情绪很复杂。有惊,有怒,有一丝微不可察的——感激。“为什么?
”“因为银子到了清河庄之后去了哪里,和王爷没有关系。”她听懂了。
我没有把宋氏牵出来。“你想要什么?”“姐姐,”我在床边坐下,“我不想要什么。
但我想知道一件事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。“当年我娘得了急症,侯府请大夫请了三天才到。
那三天里,是谁拦着不让请的?”姐姐的脸一下子白了。“我……”“姐姐不用现在回答。
”我站起来,“但这件事,我总要知道。”我转身走了。身后传来她的声音,很轻。“锦书。
”我停下脚步。“那件事……不是我。”我没回头。我知道不是她。她那年才十一岁。
但她知道是谁。10、中馈全权到手之后,我做的第一件事,是裁人。不是大刀阔斧地裁。
是把那十六个虚报在册的名字划掉,然后重新核定每个人的职责。做事的留,偷懒的罚,
吃空饷的退。一个月下来,王府的月支出从原来的一百九十多两降到了一百三十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