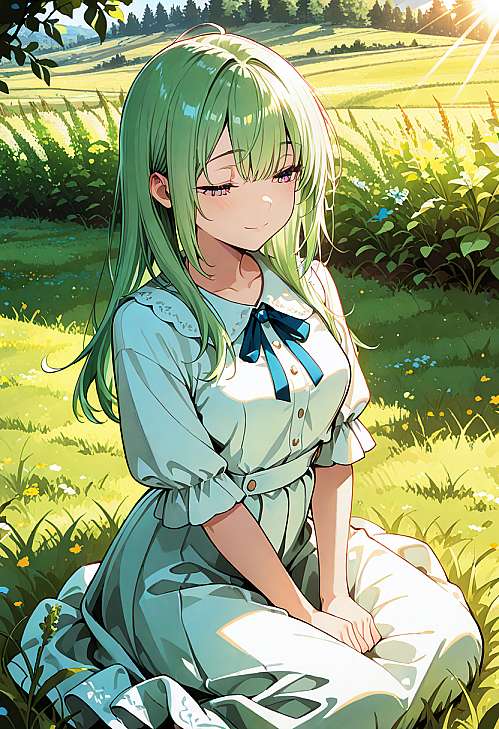贤妃娘娘将那叠银票推到我面前时,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完了,东窗事发,要噶了。
我一个假太监,在宫里给人画“先人遗像”赚外快,这事儿终于兜不住了。可她接下来的话,
却让我觉得,噶了都算是轻松的。“我不要画,”她红唇轻启,眼波流转,“我要活的。
”“我要你,今晚变成他。”那天起,我一个三流画师,
在后宫接起了“职业白月光”的活儿。我以为最大的风险是掉脑袋,后来才发现,
真正的风险,是皇帝本人也成了我的客户。这后宫,真是越来越有判头了。01我叫常安,
一个在宫里讨生活的画师,兼职假太监。说好听点是翰林图画院的待诏,
说难听点就是个宫廷美工,没品没阶,工资月光。为了攒够钱出宫娶媳妇,
我不得不干点私活。比如,给那些寂寞的娘娘们画她们进宫前“夭折”的白月光。活儿不难,
给钱也大方,唯一的风险就是要伪装成太监出入后宫。为此,我特意学了公鸭嗓,
走路微微弓着腰,见了谁都堆着一脸谦卑的笑。今天这位主顾,是皇帝新宠的贤妃娘娘。
她把我约在偏僻的落梅轩,见面第一句,就是指着桌上一幅半成品仕女图问我:“常画师,
你看本宫美吗?”我眼观鼻心,用练习过无数次的语调回道:“娘娘国色天香,乃人间绝色。
”废话,不美能当上贤妃?她却摇了摇头,葱白的手指抚过画上人的眉眼,
幽幽地说:“可皇上说,我这双眼睛,像极了已故的元后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懂了,
又是一个替身文学的受害者。皇上这是搞“宛宛类卿”那套呢。“所以,本宫想请常画师,
为元后作一幅画。”她说着,将一叠厚厚的银票推了过来,“本宫要知道,
自己到底输在哪了。”这活儿有风险啊。私自画元后,让皇上知道了,
我这脑袋可就真成“先人遗像”了。我正想找个借口推了,贤妃却忽然话锋一转。“常画师,
你在宫外,是不是有个相好?”我头皮一炸,手里的画笔差点没拿稳。
“娘娘……奴才……奴才不懂您的意思。”我开始飙演技,一脸惶恐和茫然。她笑了,
那笑容里带着看透一切的笃定:“别装了。上个月,你在宫门口托人给你那小青梅送钗子,
钗子上的流苏,还是本宫赏给洒扫宫女的。”完了,这下是真完了。假太监的身份要是暴露,
都不用皇上动手,管事的大太监就能把我片成肉片。我“扑通”一声跪下,
冷汗瞬间就下来了。“娘娘饶命!奴才……奴才也是一时糊涂!”“起来吧,”她没看我,
依旧盯着那幅画,“本宫若想害你,现在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”她顿了顿,声音压得极低,
像情人间的呢喃,说出来的话却让我浑身发毛。“本宫不要元后的画像了。”“本宫要你,
今晚,变成他。”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画纸,在我面前缓缓展开。
画上是一个穿着戎装的少年将军,剑眉星目,意气风发。虽然画技略显青涩,但那股子神韵,
简直活了过来。“他叫梁骁,是我的表哥,也是……我的心上人。
”贤妃的眼神瞬间就软了下去,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柔情,“三年前,他战死沙场。我入宫,
也是为了家族。”我大概明白了。这位娘娘思念情郎,但又不能宣之于口,
于是想找我这么个替身,来一场角色扮演。这也太……刺激了吧?“娘娘,
这……这万万不可啊!”我连连磕头,“这是欺君之罪,要诛九族的!”“富贵险中求。
”贤妃蹲下身,捏住我的下巴,强迫我抬起头,“你的脸型,跟他有七分像。你的手,
是个画师的手,仿他的字迹想必不难。最重要的是,你是个男人。”最后四个字,
她咬得特别重。我打了个哆嗦。“本宫查过了,元后之所以是皇上的白月光,
就是因为她懂皇上。她能在皇上谈论前朝时,递上一杯热茶;能在皇上批阅奏折时,
安静地陪在一旁磨墨。她给的,是陪伴,是情绪价值。”情绪价值?这词儿新鲜。
“本宫不懂那些,”贤妃的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,“但本宫知道,本宫想要的,是什么。
”“成了,本宫保你和你那小青梅后半生衣食无忧,送你们出京,天高海阔。”“败了,
”她松开手,站起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我,“你就不是假太监了,是真太监。
”我趴在冰冷的地面上,脑子飞速运转。一边是荣华富贵,和心上人双宿双飞。
一边是身首异处,或者没了命根子。这选择题,根本没得选。看着她志在必得的眼神,
和桌上那叠能让我少奋斗二十年的银票,我一咬牙,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:“……几点?
”02接下这趟活,我才明白什么叫专业。贤妃娘娘直接把一箱子东西搬到了我的画室,
里面全是那位梁骁将军的生平遗物。书信、兵法、穿旧的软甲,甚至还有一把断了的佩剑。
“从现在到戌时,你有三个时辰的时间。”贤妃像个严苛的考官,
“你要把他给我‘吃’下去,不仅要像,还得是。”我拿起一封信,纸张已经泛黄。
字迹龙飞凤舞,力透纸背,看得出是个性格张扬的人。信里的内容大多是军中趣事,
偶尔会夹杂几句对“婉妹”的思念。“婉妹”就是贤妃的闺名。我一边模仿着他的字迹,
一边听贤妃念叨他的各种习惯。“他不喜欢喝太烫的茶,总要晾一晾。”“他思考的时候,
喜欢用右手食指敲桌子,三下一组。”“他叫我‘婉妹’的时候,尾音会微微上扬。
”我听得头皮发麻,这哪是角色扮演,这简直是夺舍啊!“最重要的一点,
”贤妃突然严肃起来,“他右边眉骨上,有一道寸长的浅疤。是他十三岁时为了救我,
被马蹄踢的。”我摸了摸自己的眉骨,光滑一片。“这个好办。
”作为一个人体彩绘……哦不,宫廷画师,画一道以假乱真的疤痕,是我的基本功。
我用特制的胶和颜料,很快就在眉骨上复制了一道疤。对着铜镜一照,我自己都吓了一跳,
那疤痕微微凸起,皮肉的纹理都清晰可见,仿佛真的经历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伤害。
贤妃看着我的脸,眼神有片刻的恍惚。她递给我一套玄色劲装,正是画中梁骁常穿的款式。
换上衣服,束起长发,再把公鸭嗓换回我本来的声音,压低声线,对着镜子里的自己,
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:“婉妹。”镜子里的人,英气逼人,
眼神里带着几分少年人的桀骜不驯。我自己都信了。戌时一到,我跟着贤妃的贴身宫女,
一路低着头,来到了她的寝宫——景仁宫。宫殿里熏着清淡的龙涎香,
大部分宫女太监都被遣散了,只留下两个心腹。我深吸一口气,推门而入。
贤妃已经换下了一身华服,穿着少女时期的常服,坐在窗边,手里捧着一本书,安安静静地,
像一幅画。听到动静,她抬起头。在看到我的那一刻,她手里的书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上。
她的眼睛瞬间就红了,嘴唇哆嗦着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按照排练好的剧本,
一步步朝她走去。我没有立刻说话,而是走到桌边,提起茶壶,给自己倒了杯茶。我没喝,
只是静静地看着茶水的热气升腾,然后伸出右手食指,在桌上轻轻敲了三下。“哒、哒、哒。
”声音不大,却像三记重锤,敲在了贤妃的心上。她的眼泪,终于忍不住,
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。“表……表哥?”她试探着,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。我放下茶杯,
转过身,看着她,我看着她,露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笑容。我没有回答她是不是,
而是用宠溺又无奈的语气,缓缓开口,尾音微微上扬。“婉妹,怎么还是这么爱哭鼻子?
”贤妃再也忍不住,扑过来紧紧抱住我,哭得撕心裂肺。我身体僵硬,任由她抱着。
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这钱,真特么不好赚。这场戏,一直演到深夜。我陪她下棋,
给她讲我临时编造的“军中趣事”,甚至还按照她的要求,用梁骁的笔迹,
给她写了一封“迟到三年的情书”。看着她时而哭、时而笑,完全沉浸在我制造的幻梦里,
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既有欺骗人的负罪感,又有一种作为“造梦师”的诡异满足感。子时将至,
我必须得走了。“我该走了,婉妹。”我站起身。“别走!”她一把拉住我的袖子,
眼神里满是乞求,“再陪我一会儿,就一会儿。”“军令如山。”我轻轻挣开她的手,
说出了今晚最关键的一句台词,“我答应你,下次休沐,一定回来看你。
”这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。梁骁已经死了。但对于此刻的贤妃来说,
这却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希望。她愣住了,随即缓缓松开手,脸上露出了一个含泪的微笑。
“好,我等你。”我转身,大步流星地离开,没有回头。我怕一回头,就穿帮了。
溜回我那破旧的画室,我脱下那身玄色劲装,用湿布巾狠狠擦着脸上的妆。
眉骨上那道“疤”被我搓得生疼。看着铜镜里自己那张平平无奇的脸,我长长吐出一口气。
总算是应付过去了。我把银票塞进床底的暗格,心里盘算着,再干两票,就凑够钱了。然而,
我刚躺下没多久,房门就被人“笃笃笃”地敲响了。我一个激灵坐起来,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谁会在这个时辰来找我?“谁?”我压着嗓子问。
门外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女声:“常……常公公,您睡下了吗?
”这声音……是住在储秀宫的荣贵人身边的宫女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
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披上衣服,打开一条门缝,警惕地看着她。
小宫女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,但还是壮着胆子,塞给我一个沉甸甸的荷包。
“我家娘娘……也想要一幅画。”她顿了顿,又补充道:“活的。”我:“……”不是吧,
这业务还带人传人的?03我看着手里的荷包,脑子嗡嗡作响。荣贵人,我知道她。
一个从八品选秀上来的小姑娘,家里没什么背景,人也胆小怯懦,在宫里跟个透明人似的,
皇帝一个月都想不起她一次。她能有什么白月光?“你家娘娘……想画谁?”我试探着问。
小宫女的脸“唰”地一下红了,头埋得更低:“是……是她入宫前邻家的书生哥哥。”得,
又一个。这后宫简直是白月光重灾区。“可我……”我正想拒绝,
小宫女“扑通”一声就跪下了。“求求您了,常公公!”她带着哭腔,
“娘娘快在宫里熬不下去了。她说,要是再见不到他,她就……她就活不下去了!
”我头疼地揉了揉眉心。这叫什么事儿啊。我一个画画的,
怎么还兼职起心理疏导和临终关怀了?“你先起来。”我把她扶起来,
“这事儿……我得考虑考虑。”“这是定金。”小宫女把荷包又往我手里塞了塞,
“事成之后,还有重谢。我家娘娘说了,她什么都不要,
只要……只要您能穿着他最爱穿的月白色长衫,陪她安安静静地在庭院里,下一盘棋。
”要求还挺具体。我掂了掂荷包,分量不轻。再想想我那还没影儿的媳妇本……“行吧。
”我叹了口气,“资料呢?”小宫女大喜过望,连忙从怀里掏出一本诗集。
书页里夹着一张小像,画中人眉清目秀,文质彬彬,一股子书卷气。嗯,
跟我本人气质还挺搭。这活儿,能接。于是,我的“白月光cosplay”业务,
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了第二单。为了避免串戏,我给自己定了几个规矩。一,
不同角色坚决不在同一天接单,以免精神分裂。二,业务范围仅限深夜,天亮前必须撤。三,
每次“扮演”前,必须收一半定金,结束后结清尾款,概不赊账。四,
坚决不发生任何业务范围之外的肢体接触,我是有职业操守的。
扮演书生的难度比扮演将军低多了。我只需要换上一身月白长衫,
把头发用一根玉簪松松垮垮地束在脑后,再把说话的语速放慢一半,时不时掉两句书袋,
就齐活了。那天晚上,我在荣贵人的小院里,陪她下了一整夜的棋。她不像贤妃那么激动,
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,偶尔抬起头看我一眼,眼神里就充满了光。那一刻,
我觉得自己不像个骗子,倒像个普度众生的活菩萨。从那以后,我的业务算是彻底打开了。
今天给李昭仪扮她一去不复返的江湖侠客,明天给陈美人演她家道中落的青梅竹马。
我在各种身份之间无缝切换,演技日益精湛。我的客户群体也从娘娘们,
逐渐下沉到了各宫有头有脸的大宫女。她们的要求五花八门,扮演的对象也是千奇百怪。
有货郎,有小兵,甚至还有个想看自家哥哥的,说她哥每次都给她带糖葫芦。那天晚上,
我扛着一根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子,蹲在御花园墙角,陪着那个小宫女,吃了一晚上的糖葫芦。
甜得我发齁。后宫的夜晚不再寂寞,我的钱包也越来越鼓。
我甚至开始有点享受这种双面人生了。白天是点头哈腰的常公公,晚上是风流倜傥的白月光。
刺激。然而,我忘了,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尤其是皇宫这个八卦集散地。很快,
宫里就开始流传一个诡异的传说。说深夜的御花园里,总有一个神秘的男子出现,
他时而作将军打扮,时而作书生模样,满足怨女们的各种心愿。有人说他是鬼,
有人说他是仙。但更多的人,开始在私底下,称呼他为“后宫公共白月光”。
我听到这个外号的时候,正在给我的新客户——淑妃娘娘画眉。她要我扮演的是一个戏子。
我手一抖,眉笔差点戳她眼睛里。“公共白月光?”我干笑道,
“这……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。”淑妃对着镜子,满意地看着自己英气十足的眉毛,
轻笑一声:“怎么,你不好奇?”我怎么会好奇,那不就是我本人吗!“奴才一个阉人,
好奇这个干什么。”我赶紧撇清关系。“我倒是挺好奇的。”淑妃站起身,在屋里踱步,
“这宫里的女人,心里都苦。要真有这么个人,能给她们一点念想,倒也不是件坏事。
”她突然停下脚步,回头看我,眼神锐利。“不过,要是让皇上知道了,
有人敢在他的后宫里,给他戴这么多顶绿帽子……”她没说下去,但意思不言而喻。
我心里一紧,额头开始冒汗。最近风声是有点紧。巡夜的禁军多了两队,
好几次我都差点跟他们撞上。看来这活儿,得先停一停了。然而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
我这边还没决定金盆洗手,一个天大的“订单”,就直接砸我脸上了。
那天我正在画室里盘点我的小金库,想着什么时候实施“胜利大逃亡”计划,
大太监王喜亲自来了。王喜是皇帝跟前的红人,平日里眼高于顶,
今天却对我笑得跟朵菊花似的。“常画师,收拾一下,跟咱家走一趟。”“王总管,
这是……”“好事儿!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,神秘兮兮地说:“皇上,要见你。”我腿一软,
差点跪下。皇上?他见我干什么?难道是东窗事发了?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一百零八种酷刑。
完蛋了,我的小青梅,我的荣华富贵,我的职业生涯……全都要结束了。04我两股战战,
几乎是被王喜给拖进乾清宫的。一路上,我拼命回想最近的“业务”有没有留下什么破绽。
给贤妃写的信,烧了。陪荣贵人下的棋,收了。扛着糖葫芦草靶子在御花园裸奔……哦不,
是徘徊,那天晚上雾大,应该没人看清我的脸。应该……万无一失吧?我怀着上坟的心情,
走进了乾清宫。殿内灯火通明,檀香袅袅。年轻的皇帝,玄昭,正坐在书案后,
低头批阅奏折。他穿着一身明黄色的常服,没戴冠,墨色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,
少了几分朝堂上的威严,多了几分说不出的……寂寥。听到动静,他抬起头。
那是一张极其英俊的脸,剑眉入鬓,凤眼狭长。只是眼神过于深邃,像一潭不见底的古井,
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。我不敢与他对视,赶紧跪下磕头。“奴才常安,叩见皇上,
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“起来吧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,听不出喜怒。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,
头埋得更低了,恨不得当场表演一个缩头乌龟。“抬起头来。”他又说。我心一横,
死就死吧。缓缓抬起头,迎上他的目光。他也在看我。那目光像是带着实质的重量,
从我的眉毛,到我的鼻子,再到我的嘴唇,一寸一寸地扫过。
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摆在案板上的猪肉,任人估价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
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就在我快要绷不住的时候,玄昭终于开口了。“王喜说,
你画人像,堪称一绝?”我心里松了半口气。原来是问画画的事,还好还好。“奴才不敢当,
只是一些糊口的浅薄技艺。”我谦卑地回答。“哦?”他挑了挑眉,“朕听说,
你画的‘遗像’,能让活人看了都信以为真?”我心里又咯噔一下。
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?“奴才……奴才只是尽力揣摩神韵罢了。
”“神韵……”玄昭重复着这两个字,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,“好一个神韵。
”他从书案上拿起一张画纸,递给王喜。王喜又把画递给我。“你看看,此人,
你可能画出他的‘神韵’?”我双手接过画,低头一看,瞬间愣住了。画上的人,
是一个穿着铠甲的将军。但不是贤妃的白月光梁骁。这位将军看起来年纪稍长,面容刚毅,
眼神中带着化不开的忧郁。最特别的是,他的左眼眼角,有一颗小小的泪痣。这人我不认识。
但我敏锐地发现,他的脸型和五官,竟然和御座上的那位,有七八分的相似。
简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“此人是朕的亲兄长,已故的裕亲王。
”玄昭的声音从上方传来,带着一丝飘忽,“他战死于北境,连一幅完整的画像都未曾留下。
这幅,还是凭着宫中老人的回忆,拼凑出来的。”我明白了。
皇帝这是想让我给他哥画一幅更逼真的遗像。这活儿,我熟啊!“皇上放心,
奴才定当竭尽所能!”我立刻表忠心。玄昭却摇了摇头。“朕不要画像。”我心里一突,
一种极其荒谬且恐怖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不会吧……不会吧?他缓缓站起身,
一步步走到我面前,高大的身影将我完全笼罩。他弯下腰,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,
在我耳边说:“朕听说,后宫里有个‘公共白月光’,能扮成任何人。”我的血,
在那一瞬间,凉了。他知道了。他什么都知道了!我“扑通”一声再次跪下,
浑身抖得像筛糠。“皇上饶命!皇上饶命啊!”“哦?饶你什么命?”他好整以暇地看着我,
语气里带着玩味,“是饶你假扮太监,私入后宫之罪?
还是饶你……给朕戴了满后宫的绿帽子之罪?”我大脑一片空白,除了磕头,什么也做不了。
“奴才罪该万死!奴才罪该万死!”“起来。”他淡淡地说。我不敢动。“朕叫你起来。
”他的声音冷了几分。我颤抖着爬起来,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尿裤子。他绕着我走了一圈,
像是在审视一件货物。“胆子不小,演技也不错。”他停在我面前,伸手,
用指尖点了点我的眉骨,“贤妃的少年将军,荣贵人的穷书生,
还有李昭仪的江湖客……”他每说一个,我的心就凉一分。“常安啊常安,你可知,
欺君罔上,是何等大罪?”“奴才……知罪。”我闭上眼睛,等待着雷霆之怒。然而,
预想中的“拖出去斩了”并没有到来。玄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“罢了。
”他转身走回书案后,重新坐下,神情看起来有些疲惫。“朕的后宫,死气沉沉,
像一潭死水。你倒是厉害,一个人,搅动了整池春水。”我愣住了,
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夸我?“你很有用。”他看着我,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,“所以,
朕不杀你。”我还没来得及高兴,他就抛出了后半句。“朕,要你给朕,也干一票。
”我:“???”幻觉,一定是幻觉。皇帝,九五之尊,天底下最尊贵的男人,
竟然要我……给他提供“白月光cosplay”服务?我一定是在做梦,一个噩梦。
“朕要你,扮成他。”他指了指那幅裕亲王的画像,“陪朕,喝一晚上的酒。”我张了张嘴,
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这世界,太疯狂了。05我,常安,一个平平无奇的宫廷画师,
竟然接到了来自皇帝本人的“白月光订单”。这事儿说出去,谁信?可它就这么发生了。
我被王喜“请”进了一间偏殿,好吃好喝地伺候着,待遇堪比娘娘。唯一的任务,
就是研究那位已故裕亲王的资料。玄昭给我的资料,比贤妃那一箱子东西专业多了。